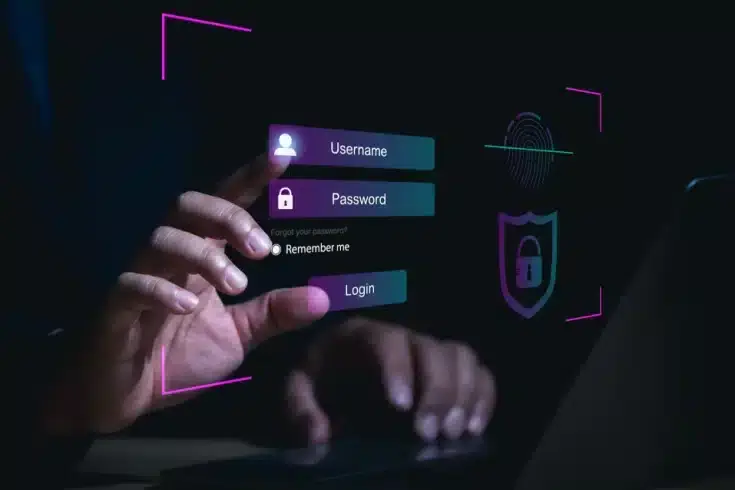在日本合同会社中员工的权利:从利润分配到参与经营

自2006年(平成18年)日本公司法施行以来,合同公司(Godo Kaisha,LLC)因其成立简便和运营灵活,成为众多企业家的首选公司形态。特别是,这种借鉴美国LLC(有限责任公司)模式引入的公司形态,对于考虑国际业务拓展的企业来说,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选择。理解合同公司的关键概念之一是“社员”的地位。与株式会社的“雇员”不同,合同公司的“社员”指的是向公司出资的成员,即所有者。这一地位虽与株式会社的股东相似,但有一个决定性的不同,即合同公司原则上以“所有权与经营权一致”为前提。也就是说,作为出资者的社员原则上亲自承担公司的经营管理。这一基本结构大幅定义了社员所享有的权利内容。本文将深入解析合同公司社员所拥有的“持分”,即对公司的权利与义务的集合体,从社员从公司获得经济利益的权利(自益权)和参与、监督公司经营的权利(共益权)两个方面,阐明日本公司法如何规定并保护这些权利,结合具体法条和裁判例进行详细说明。
合伙公司中员工权利全貌:个人利益权与共同利益权
在日本合伙公司中,员工所持有的权利根据其性质可以大致分为两大类。这是依据日本公司法的传统分类方法,也用于解释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权利。一类是“个人利益权”(自益権),另一类是“共同利益权”(共益権)。
个人利益权(自益権)指的是员工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对公司行使的权利。包括要求分配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利润、以及在公司解散时分配剩余财产的权利。这些权利是作为员工出资的直接回报。
另一方面,共同利益权(共益権)指的是员工为了公司整体利益而参与公司经营或监督管理的权利。具体包括执行公司业务的权利和调查业务执行状况的权利。共同利益权不仅关注个别员工的利益,也旨在保障作为共同事业体的公司本身的健全运营。
在股份有限公司中,所有权(股东)与经营权(董事)是分离的,因此个人利益权(如股息收取权)与共同利益权(如股东大会的表决权)相对明确区分。然而,在原则上所有权与经营权一致的合伙公司中,这两种权利的界限更为流动。例如,执行业务的权利(共同利益权)直接源自员工作为所有者的地位,而通过行使这一权利所产生的利益,最终通过个人利益权回馈给员工。理解这种相互关系是掌握合伙公司权利结构的关键。
在日本法下员工自益权的具体内容
员工自益权的核心,在于享有公司利益的权利。日本公司法(Japanese Corporate Law)规定了这一权利,主要从“损益分配”和“利润分配”两个方面进行定义。这两者虽然紧密相关,但在法律含义和程序上存在重要差异。
損益分配
損益分配是指在会计期间结束时,确定公司的利润或亏损,并决定如何以及以何种比例分配给各个股东的过程。这一分配比例是确定股东间经济关系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根据日本公司法(日本法)第622条第1款的规定,如果章程中没有关于損益分配比例的具体规定,那么分配比例应根据各股东的出资额来确定。这意味着出资额较大的股东将承担更多的利润(或亏损)。
然而,合同公司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可以通过“章程自治”灵活地改变这一原则。股东可以通过章程达成一致,自由决定与出资额完全不同的損益分配比例。例如,如果A股东是资本提供者,而B股东提供了优秀的技术或专业知识,即使B股东的出资额较少,也可以根据其贡献度设定比A股东更高的利润分配比率。这种灵活性是合同公司在多样化贡献形式的共同事业中受到青睐的原因。
此外,日本公司法第622条第2款规定,如果章程仅对利润或亏损的分配比例作出规定,那么该比例被推定适用于利润和亏损。这是对当事人合理意图的一种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当亏损被分配时,并不意味着立即要求额外的出资。通常情况下,如果章程中没有特别规定,亏损金额将通过减少各股东持股的账面价值来处理。这一结果将影响股东退出公司时的持股回购金额,以及公司清算时的剩余财产分配金额。
利益分配
与会计上的损益分配确定利益归属不同,利益分配是指实际将公司财产分配给股东的行为。根据日本公司法(日本法)第621条第1款的规定,股东有权向公司索取利益分配。
相较于株式会社的“剩余金分配”可以以利益剩余金和资本剩余金为基础,合伙公司的“利益分配”则仅以利益为基础。这一点也是保护公司财产的重要差异。
关于利益分配的程序,合伙公司具有较高的灵活性。法律上原则上股东可以随时请求利益分配,但这可能会导致公司资金流动性变得不稳定。因此,在实务操作中,通过公司章程具体规定利益分配的时间、次数和程序等是极其重要的。例如,可以设定规定如“在业务年度末的确定决算后,由执行业务的股东过半数决定进行分配”,以实现计划性的财产分配。
然而,这种分配自由受到严格的法律限制,即所谓的“资金来源规制”。日本公司法(日本法)第628条规定,如果分配金额超过了分配当日公司的利润金额,公司则不能进行该利润分配。这是为了防止公司财产被不当流出,损害公司债权人的绝对规则。公司有权也有义务拒绝违反此规制的分配请求。
如果公司违反了这一资金来源规制进行了分配(非法分配),其责任是严重的。根据日本公司法(日本法)第629条第1款,执行该分配业务的股东需与接受非法分配的股东连带负责,向公司支付相当于分配金额的款项。除非执行业务的股东能证明自己在职责执行上没有疏忽,否则无法免除此责任。这种责任的免除通常需要全体股东的同意,但也仅限于分配时存在的利润金额范围内。此外,公司的债权人也可以直接向接受非法分配的股东索要支付。由此可见,利益分配的灵活性背后,股东和管理者双方都承担着严格的财产保全责任。
共益权的具体内容:参与和监督经营的权利
共益权是指作为公司所有者的社员,如何参与公司经营以及如何进行监督的权利。在所有权与经营权一致的合伙公司中,共益权的设计是治理结构的核心。
业务执行权和代表权
日本公司法对合伙公司的业务执行和代表权首先设定了原则,然后允许通过公司章程进行定制。
根据日本公司法(日本公司法第590条第1款)的原则,社员都有权执行公司业务(业务执行权)。如果有多个社员,除非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否则公司业务应由社员过半数决定(同条第2款)。此外,原则上执行业务的社员也有代表公司的权力(代表权)(日本公司法第599条第1款、第2款)。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特别规定,所有社员都是执行业务的社员,同时也是代表社员。
然而,所有社员都参与经营决策和对外合同行为可能会效率低下,或者责任归属不明确。因此,日本公司法允许通过公司章程集中权力。可以在公司章程中指定特定的社员为“业务执行社员”。在这种情况下,业务执行权限于被指定的业务执行社员,其他社员则不参与经营决策。业务决策由业务执行社员过半数进行(日本公司法第591条第1款)。
此外,还可以从业务执行社员中指定特定的人为“代表社员”。一旦指定了代表社员,代表公司的法律权力就集中在代表社员身上,其他业务执行社员则只负责内部业务执行。如果法人是社员,那么该法人需要选任一名自然人作为“职务执行者”,并进行登记。
监督和调查权
即使是没有业务执行权的社员,也就是从一线经营中退下来的出资者,也保留了保护其投资的重要权利。这就是调查公司业务和财产状况的权利。
日本公司法第592条第1款明确规定,即使没有业务执行权的社员,也可以调查公司的业务和财产状况。这是一项非常强大的权力,用于监督业务执行社员的业务执行,检查不正当行为或经营失误。
考虑到调查权的重要性,法律规定不得轻易剥夺这项权利。日本公司法第592条第2款虽然允许公司章程对这项调查权另有规定,但附带条件是“不得规定在事业年度结束时或有重要事由时限制依据前款规定进行调查”。这意味着,即使是公司章程,也不允许剥夺社员的基本监督权。这一规定对于少数派社员或不参与经营的投资者来说,是保护其出资份额的重要安全阀。在后面提到的判例中,这项调查权的侵犯也成为了重大的争议点。
在日本的合同会社与株式会社(KK)的权利比较
通过比较合同会社的社员权利与日本最常见的公司形态——株式会社(KK)的股东权利,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理解前者的特点。两者之间的差异源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关系的根本不同。
株式会社(KK)以“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为原则,出资者即股东将经营权委托给专业的董事。股东的权利主要通过在股东大会上行使表决权间接影响经营,以及获得分红。
相反,合同会社以“所有权与经营权一致”为原则,出资者即社员亲自承担经营。因此,其权利更为直接和灵活。例如,利润分配不受出资比例限制,可以通过章程自由决定。决策也可以不经过股东大会这样的正式程序,通过社员间的协议迅速进行。转让持份需要得到其他所有社员的同意,这体现了公司在人际信任关系上的封闭性结构。
以下表格总结了这些主要差异:
| 特征 | 合同会社 | 株式会社(KK) |
| 利润分配原则 | 可通过章程自由决定 | 原则上按出资比例 |
| 决策机构 | 原则上需所有社员同意或过半数 | 股东大会 |
| 表决权基础 | 原则上按社员过半数(人数)决定(可通过章程修改) | 原则上一股一表决权 |
| 经营者 | 执行业务的社员(原则上为所有社员) | 董事 |
| 所有权与经营权关系 | 一致 | 分离 |
| 持份转让 | 需要其他所有社员的同意 | 原则上自由(除非是限制转让的股份) |
从这一比较中可以看出,合同会社适合基于人际信任关系、追求灵活和迅速经营的小规模合作企业,而株式会社(KK)则适合广泛集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大规模企业运营。
员工间的纠纷与裁判例:在日本法下的员工除名
合伙企业的灵活性和封闭性,在员工间的信任关系得以维持时,可成为巨大的优势。然而,一旦这种信任关系崩溃,就可能导致严重的经营停滞和对立,蕴含着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最终的法律手段是利用“除名”制度,强制将问题员工排除出公司。
日本公司法(日本法)第859条规定,如果员工存在不正当行为或严重的义务违反等不可避免的理由时,公司可以基于其他员工过半数的决议,提起诉讼请求除名该员工。关于“不可避免的理由”如何解释,两个对照的裁判例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首先,关于除名请求未被接受的案例,有东京地方法院2019年7月3日的判决。该案件涉及一家由夫妻两名员工组成的合伙企业,妻子即员工A请求除名丈夫即代表员工Y。A声称Y伪造了A的签名并制作了财务报表,且未应A的会计账簿查阅请求,将这些作为除名的理由。然而,法院驳回了这一请求。最主要的原因是,公司的业务实质上完全依赖于Y一人的活动,如果除名Y,将严重妨碍公司业务的持续。法院虽然认为Y的行为是有问题的,但也指出这更多是夫妻间的对立带入了公司,认为排除Y对于公司的存续并非“不可避免”。
其次,关于除名请求被接受的案例,有东京地方法院2021年11月29日的判决。该案件同样涉及由两名员工组成的合伙企业,其中一名员工(法人)的职务执行者私自挪用了公司资金,进行了严重的不正当行为。另一名员工以此不正当行为为由,请求除名犯错的职务执行者所属的法人员工。法院接受了这一请求。判决认为,资金的私自挪用行为明确符合公司法第859条第3号“在执行业务时进行了不正当行为”,这破坏了员工间的信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不正当行为的严重性超过了除名对业务的影响,为了公司的健全存续,排除犯错的员工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
这两个裁判例表明,法院在做出除名判断时,不仅考虑行为的形式上的非法性,还综合考虑了该行为对公司业务持续的影响以及对员工间信任关系的破坏程度等实质性因素。特别是,对于威胁到公司存续的严重不正当行为(如挪用资金)与经营上的意见分歧或监督权未行使等问题之间,法院划出了明确的界限。这提示员工,除名这一最终手段只能非常有限地使用,同时也表明,在纠纷加剧之前,通过章程规定的程序和协商解决问题对于保护自身权利的重要性。
总结
本文全面解释了在日本合同公司中员工权利的问题,从自益权和共益权的角度进行了详细阐述。合同公司最大的魅力在于其运营的灵活性,这得益于公司章程自治原则的支持。从利润分配方法到经营体制的设计,员工可以通过共同协议自由塑造公司的形态。然而,这种自由并非无限制。为了保护债权人,法律设定了严格的财源规制,并保障了对业务执行者的监督权,这些都是维护公司健全性的重要框架。正如判例所示,一旦员工间的信任关系崩溃,法律解决将变得困难,因此最重要的风险管理在于,在业务开始时,所有员工都能接受的明确且详细的公司章程的制定。其中应具体包含每位员工的权利与义务、决策过程,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争议解决方法。
Monolith法律事务所拥有为国内外众多客户提供从合同公司设立、运营到争议解决等丰富法律服务的经验。我们事务所不仅有持有日本律师资格的专家,还有持有外国律师资格的英语专家,他们能够从国际视角为客户的业务构建最佳治理结构提供支持。如果您需要关于员工权利等复杂问题的专业建议,如本文所述,请随时咨询我们的事务所。
Category: General Corpor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