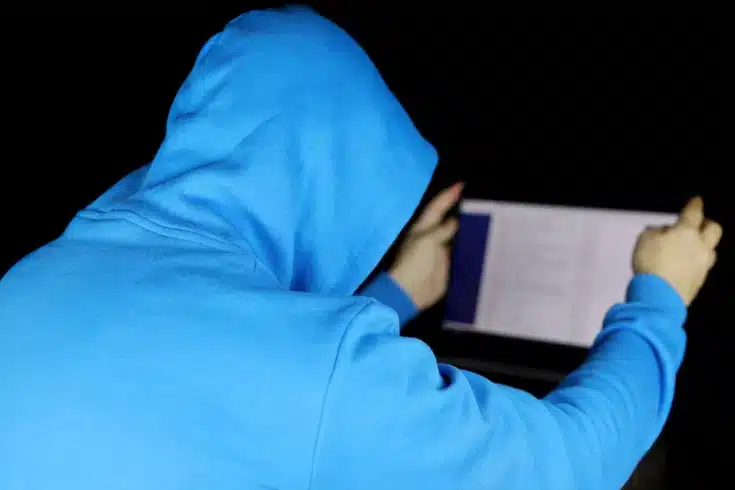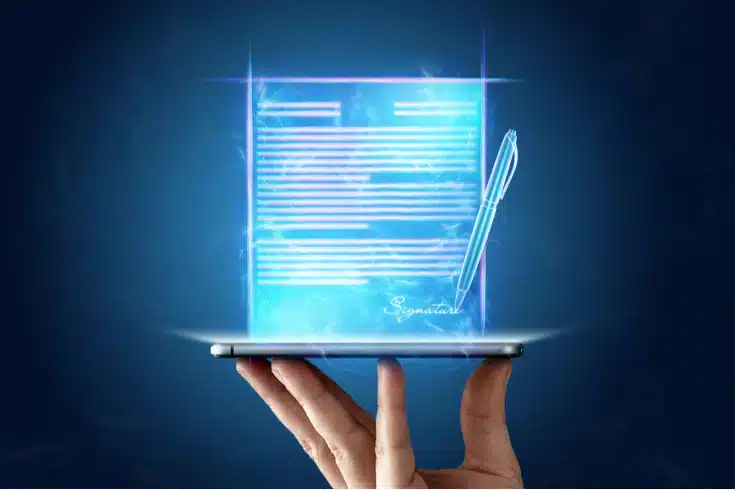解读日本公司法中的破产程序

企业经营有时会面临严重的财务困难。为了应对这类危机情况,日本的法律体系提供了一套精细的法律框架,不仅仅是将其作为业务失败而结束,而是旨在寻求有序的解决方案。这个框架主要分为两个战略方向。一是以整理公司资产并公平分配给债权人为目的的“清算型”程序;另一是以业务持续为前提,重构财务内容和组织结构,以实现复兴的“重建型”程序。这些法律程序可以说是根据公司状况选择的战略性工具包。对于股东和经理人来说,深入理解这些选项,在危机情况下保护企业价值、履行受托责任,并做出基于信息的准确决策至关重要。本文将从专业角度解读日本破产法制下的四种主要法律程序——破产、特别清算、民事重整和公司重整——的特点、差异以及担保权的处理等重要法律议题,并结合近期的判例分析,全面阐述其整体情况。
日本破产程序的全貌
日本法律规定了四种主要的破产程序,这些程序都在法院的监督下进行。这些程序首先根据其目的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旨在停止公司的业务活动并消除其法人资格的“清算型程序”,包括破产程序和特别清算程序。另一类是在继续业务的同时寻求公司重建的“重建型程序”,民事重整程序和公司重整程序属于此类。
此外,这些程序还可以根据谁主导程序来分类。一种是被称为“管制型程序”,由法院选任的中立专家(管制人)掌握公司的经营权和财产管理处置权来推进程序。破产程序和公司重整程序属于这一类型。另一种是被称为“债务人控制型(Debtor in Possession,DIP)程序”,原则上由现有的管理层保持经营权,自行执行重建或清算程序。特别清算程序和民事重整程序属于这一类型。
这种双重分类,即选择“清算型还是重建型”以及“管制型还是DIP型”,清晰地展示了面临经营危机的企业所面临的战略性困境。选择程序不仅仅是选择法律形式,还涉及到业务的持续可能性这一经营判断,以及是否保持经营权这一重大决策。例如,如果目标是重建,管理层如果想要继续掌握主导权,可能会选择民事重整;但如果债权人或法院认为现有管理层对经营失败负有责任,可能会选择由外部管制人接管的公司重整。因此,管理层不仅需要客观评估公司的财务持续可能性,还需要评估来自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度。
在日本进行清算型破产程序:清算公司资产
清算型程序旨在公司无法继续经营时,将其资产变现,并对债权人进行公平分配,以便在法律上正式结束公司的存在。
日本的破产程序
破产程序是基于日本破产法的最基本且最有力的清算类型程序。对于法人而言,当根据日本破产法第15条规定的“支付不能”(债务人因缺乏支付能力而无法普遍且持续地支付到期债务的客观状态)或第16条规定的“债务超过”(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偿还其债务的状态)被认定时,破产程序将由法院决定启动。
一旦程序启动,法院将从中立的律师中选任一名“破产管理人”。根据日本破产法第2条第12款的规定,破产管理人将专有管理和处置公司财产的权利。这意味着现有的管理层将失去所有的经营权和财产处置权,破产管理人将执行一系列清算工作,包括调查公司资产、确保、变卖处理,以及按照法律上的优先顺序向债权人分配。
该程序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启动时不需要债权人的同意。只要法院认定了客观的破产状态,程序就会强制进行。这是一种制度设计,旨在在债权人之间的对立激烈或管理层失去信任的情况下,由中立的第三方介入以恢复秩序,并公平保护所有债权人的利益。破产管理人被赋予了一项强大的权力——“否认权”,可以使破产程序启动前进行的不公平支付无效,实质上确保了债权人平等原则的实施。因此,破产程序被定位为当其他协调性解决方案不可能时的最终选择。
特别清算程序
特别清算程序是根据日本公司法(日本平成时代(1989年)第510条及以下)规定的,仅限株式会社使用的简易清算程序。该程序首先由公司通过股东大会的特别决议解散,然后进入常规清算程序,如果存在负债超过资产的疑虑或其他严重妨碍清算执行的情况,便会启动此程序。
与破产程序不同,主导程序的不是法院指定的外部管理人,而是公司的“清算人”。清算人通常由前董事等担任,管理层保持一定的控制权,形成DIP(债务人持有财产)型的程序。
该程序的核心在于与债权人达成一致。具体来说,是在债权人集会上通过称为“协定”的还款计划,或与个别债权人达成“和解”来推进清算。协定的通过需要出席的表决权者过半数同意,且这些表决权者所持表决权的总额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同意。正如这一要求所示,特别清算前提是与主要债权人就清算计划达成事先协议的协作状态。如果无法获得债权人的同意,程序将失败,多数情况下将转入破产程序。
由于基于合意形成的性质,特别清算相比破产程序有迅速且低成本完成的优势。特别是在债权人数量有限且合作态度的情况下,如母公司清算子公司,这种程序被频繁使用。
日本破产与特别清算程序的比较
以下表格总结了日本破产程序与特别清算程序的主要区别。
| 项目 | 破产程序 | 特别清算程序 |
| 法律依据 | 日本破产法 | 日本公司法 |
| 适用主体 | 所有法人与个人 | 仅限股份公司 |
| 程序主体 | 由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管理型) | 公司的清算人(债务人自主管理型) |
| 债权人的同意 | 启动时不需要 | 通过协议时需要 |
| 期间与费用 | 一般较长期、费用较高 | 一般较短期、费用较低 |
| 主要权力 | 破产管理人的强大否决权 | 基于与债权人的协议的灵活解决方案 |
在日本进行重建型破产程序:旨在实现企业复兴
重建型破产程序旨在帮助那些虽然面临财务困境,但其业务本身具有价值且有可能继续存在的企业,实现复兴。
日本民事再生程序
日本民事再生程序是基于日本《民事再生法》的法律程序,旨在帮助债务人恢复其业务或经济生活。这一程序的最大优势在于其灵活性,不仅股份有限公司,还包括合伙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等各类经营主体均可利用。
原则上,程序采用债务人持有管理权(DIP)模式进行,现有的管理层在保持管理权的同时继续经营业务,并自行制定和执行重组计划。根据日本《民事再生法》第38条第1款的规定,一旦重组程序启动,债务人有权继续执行业务并管理及处置财产。原则上,股东的权利也不会发生变化。
然而,这一程序存在重大限制,即涉及拥有担保权的债权人(主要是金融机构)的权利处理。在民事再生程序中,担保权债权人拥有“別除权”,原则上可以不受重组程序影响,对担保资产(例如工厂或机械)进行查封并出售,以回收其债权。这意味着对于业务连续性至关重要的资产可能会丧失的风险。
因此,为了确保民事再生程序的成功,事实上不可或缺的是在申请前与主要担保权债权人进行谈判,建立合作关系,例如协商担保权的行使暂缓等。通过在债权人集会上获得过半数表决权者及表决权总额过半数的同意,重组计划得以通过,从而确定重建的道路。
日本公司重整程序
公司重整程序是基于日本公司重整法的最强大的重建型程序。由于其强大的效力,仅限于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并主要用于大型企业的重建。
该程序是管控型的,一旦启动,法院会立即选任“重整管控人”,现有的管理层将被全部撤换。公司的经营权和财产管理处置权将全部集中于重整管控人手中。
公司重整程序的最大特点是,它能够停止在民事重建程序中无法限制的担保权利行使。担保权利人不能行使排除权,其债权将作为“重整担保权”在程序中处理,并且会根据重整计划受到减额或支付延期等变更。此外,股东的权利也可以大幅度变更,在许多情况下会进行100%减资(消除现有股东的所有权利)。
因此,公司重整程序是一种制度,旨在彻底调整包括担保权利人和股东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并在外部专家即重整管控人的主导下,全面重构企业。由于其强大的效力,程序复杂,费用高昂,且耗时。对于管理层而言,选择此程序意味着自我退位,这是为了拯救业务而牺牲自己地位的重大决定。
日本民事再生与公司更生的比较
以下表格总结了日本民事再生程序与公司更生程序的主要区别。
| 项目 | 民事再生程序 | 公司更生程序 |
| 法律依据 | 日本民事再生法 | 日本公司更生法 |
| 适用主体 | 所有法人与个人 | 仅限股份公司 |
| 程序主体 | 现有管理层(DIP模式) | 法院指定的更生管理人(管理模式) |
| 担保权的处理 | 有別除权(可在程序外行使权利) | 无別除权(作为更生担保权在程序内处理) |
| 股东权利 | 原则上不变 | 可变更(包括100%减资) |
| 主要使用场合 | 中小企业、预期能与担保权人协调的情况 | 大型企业、需要根本性重建的情况 |
在日本破产程序中的担保权处理
在破产程序中,如何处理担保权是决定程序成败的极其重要的论点。
別除权
別除权是指在破产程序或民事重整程序中,拥有特定财产上担保权的债权人可以在破产程序之外行使其权利,并优先于其他债权人获得偿还的权利。这一权利的法律依据是日本的破产法第65条和日本的民事重整法第53条。
这一权利的存在对程序产生巨大影响。例如,对于寻求民事重整的公司来说,如果其核心工厂设有银行的抵押权,银行行使別除权将工厂拍卖,公司的业务连续性将变得不可能。换言之,即使法律上启动了民事重整程序,如果没有获得担保权人的合作,重建实际上就会陷入停滞。
因此,別除权的存在将破产程序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法院管理的旨在公平分配无担保债权人之间权益的正式程序。另一方面是在幕后进行的,与担保权人进行的极其重要的谈判。对于选择民事重整的管理层来说,在申请前与主要金融机构等达成“暂停行使担保权的协议”(Standstill Agreement)是成功的绝对前提条件。
更生担保权
在公司更生程序中,不承认別除权。一旦程序启动,所有担保权的执行都会被自动禁止。担保权人的权利将转变为“更生担保权”的地位,并在更生计划中与其他债权一样成为权利变更的对象。这一法律依据存在于日本的公司更生法中,例如第2条第10项定义了更生担保权,第47条规定了禁止权利行使。
正是这一机制赋予了公司更生程序强大的重建能力。通过暂停个别债权人的权利行使,并将所有利益相关者(担保权人、无担保债权人、股东)带到同一桌前,更生管理人可以为公司整体的资本结构制定全面的重建计划。这种优先考虑企业整体重生而非个别权利的公共利益思想是其基础。正因为允许对个人财产权的强烈干预,才有必要设立严格的程序要求,如中立的管理人选任和严格的法院监督,以防止滥用。
各程序中担保权的处理比较
| 程序 | 担保权的处理 | 法律依据 | 对公司及债权人的影响 |
| 破产程序 | 別除权 | 日本破产法第65条 | 债权人可以出售担保物。公司可能失去重要资产。 |
| 特别清算程序 | 別除权 | 日本公司法(一般原则) | 债权人可以出售担保物。程序依赖于债权人的合作。 |
| 民事重整程序 | 別除权 | 日本民事重整法第53条 | 债权人可以出售担保物。申请前与担保权人的谈判是必不可少的。 |
| 公司更生程序 | 更生担保权(无別除权) | 日本公司更生法第47条等 | 债权人的权利行使被暂停。债权在计划中被更改。公司获得继续经营的时间。 |
近期日本最高法院案例介绍
在破产实务领域,法律条文的解释总是不断产生新的挑战。本文将介绍近期日本最高法院的重要判决。
日本最高法院于2021年12月22日(令和3年)作出的决定,涉及对日本民事再生法第174条第2款第3项的解释。该条款规定,如果再生计划的决议是通过“不正当的方法”成立的,则法院不得批准该计划。
案件的概要是,在民事再生程序中,公司的管理人与一位持有大量债权的主要债权人签订了解决债权存否争议的和解合同。该和解合同包含了该债权人将对再生计划案行使赞成票的条款。其他债权人认为这是所谓的“买票”,属于“不正当的方法”,因此要求不批准该计划。
对此,日本最高法院判定,包含对再生计划案赞成的和解合同并不直接构成“不正当的方法”。法院应当综合考虑和解合同的签订意图和过程,以及和解内容是否整体上对再生债务人(公司)是合理的。在本案中,和解解决了复杂的争议,并且内容对公司的重建是合理的,因此不能仅仅因为它影响了投票权的行使就认为是出于“不正当的方法”而签订的。
这一判例对于破产程序中的谈判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司法机关确认了谈判的现实性。为了形成通过再生计划所需的多数派,管理人或管理层与单个债权人进行争议解决谈判在实务中是必不可少的。本决定表明,在这样的谈判中,并不是禁止以赞成计划为条件,而是应根据实质性标准来判断,即合意内容是否不公平地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以及是否对公司整体具有商业合理性。这使得实务家可以进行更加灵活的谈判,但同时也承担起构建对所有债权人都能解释并且公正的交易的责任。
总结
在日本的破产法律体系中,面临财务危机的企业可以选择“清算”和“重建”两种基本方向,并且每种方向都提供了多种程序。破产和特别清算是旨在整理公司资产并终结公司的清算型程序,而民事重整和公司重整则是以业务的持续和复兴为目标的重建型程序。这些选择紧密关联着管理权是否能够保持(自主管理型DIP)或是否交由外部专家管理(管制管理型),这是涉及经营核心的重要决策。特别是,担保权的处理(是否有排除权)是决定各程序战略价值的关键因素。为了驾驭这一复杂的法律框架并找到最佳路径,不仅需要深厚的法律知识,还需要高度的战略思维和谈判能力。
Monolith法律事务所在提供日本公司法相关服务方面,特别是企业破产程序,拥有为国内外客户提供丰富法律服务的经验。我们事务所不仅拥有日本律师资格的专家,还有持有外国律师资格的英语专家,能够在复杂的破产情况下为管理层和股东提供最大化权益的战略性建议。从清算型程序到重建型程序,我们承诺支持客户应对各种情况,并引导他们找到最佳解决方案。如果您需要法律危机管理方面的咨询,请务必联系我们Monolith法律事务所。
Category: General Corpor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