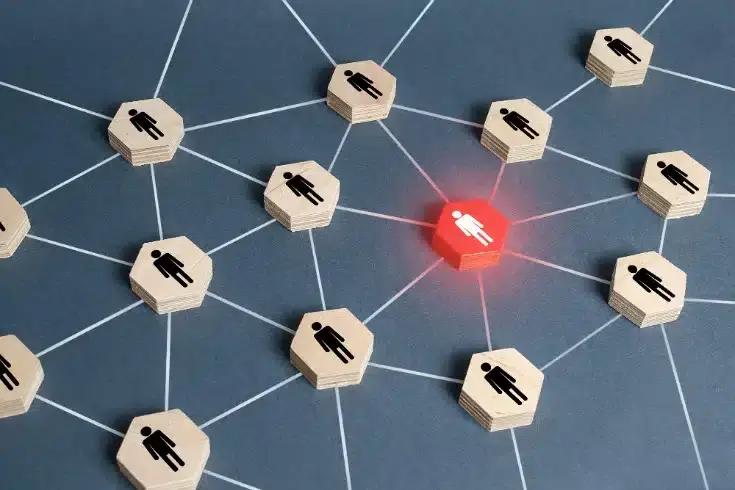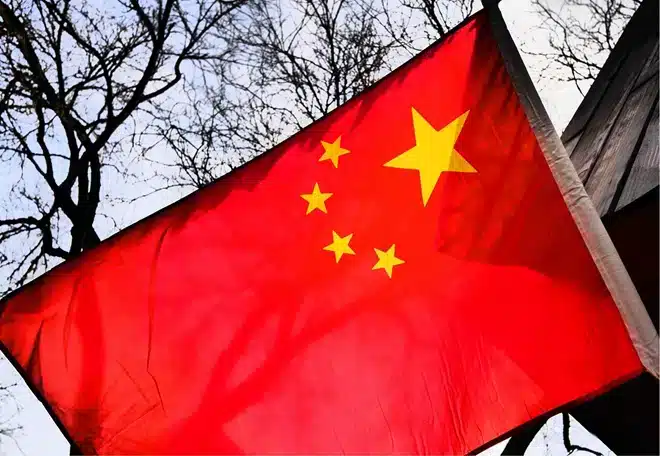在日本商法中关于仓储业务与寄存合同的法律解释

在全球供应链中,日本作为极其重要的节点发挥着功能。无论是制造业、零售业还是贸易业,许多公司都将自己宝贵的产品或原材料作为业务活动的一部分存放在日本的仓库中。这种行为不仅仅是物理存储,它还产生了一种名为“寄存”的法律契约关系。深入理解这种寄存关系,尤其是与从事仓储业务的仓库经营者之间的关系的法律制度,不仅仅是学术探究。这是管理资产保全、确保交易顺畅以及应对可能发生的风险的经营上的必要要求。日本的法律制度在这一领域设立了两个主要支柱。一个是规定寄存人与仓库经营者之间私人权利义务关系的《日本商法》。另一个是为了确保仓库行业的正当运营并保护用户利益而设立的公共监管法《日本仓库业法》。本文将揭示这两部法律如何协同作用,形成保护企业资产的框架。具体来说,我们将详细解释仓库经营者所承担的严格注意义务及其证明责任所在,仓库收据所具有的独特法律效力及其作为金融工具的功能,仓库经营者拥有的强大留置权,以及在寄存合同终止时应注意的权利义务关系和短期消灭时效等,在实务上极为重要的论点,并结合具体的法规定和裁判例进行详细说明。
日本倉儲業務的法律框架
日本的法律制度從私法和公法兩個層面對倉儲業務進行全面規範。理解這一雙重法律結構是使用日本倉庫服務的第一步。
第一個支柱是日本商法。該法律規定了寄託人(存放物品的人)和倉儲經營者(保管物品的業者)之間的私法合同關係,即寄託合同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合同內容的解釋以及寄託物的滅失或損壞時的損害賠償責任等具體法律問題主要基於日本商法來解決。
第二個支柱是日本倉庫業法。這是一部監督倉儲業務本身,旨在促進其健康發展和保護使用者利益的公法,即行政規範法。日本倉庫業法第1條明確規定了其目的:“確保倉儲業的適當經營,保護倉庫使用者的利益,並確保倉單的順利流通”。考慮到倉儲業承擔他人貴重財產的公共性,該法律對業者規定了各種義務。
公法規範的核心是向國土交通大臣的登記制度。想要經營倉儲業的人不能隨意開始業務,必須滿足法律規定的嚴格標準並正式登記。這些登記要求不僅是形式上的程序,更是保護使用者資產的實質性防護。例如,倉庫的設施和設備必須根據存儲物品的類型滿足比一般建築物更嚴格的防火、防水和防盜標準,這些標準由建築基準法和消防法規定。此外,每個倉庫還必須專任具有倉庫管理專業知識和能力的“倉庫管理主任者”。
這兩部法律的關係不僅僅是並列。公法中的日本倉庫業法所定的登記標準和經營義務也會影響私法中日本商法規範的合同關係。例如,如果寄託物在火災中被燒毀,寄託人可以根據日本商法向倉儲經營者索賠。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倉儲經營者未滿足日本倉庫業法規定的防火標準,這一事實將成為證明日本商法上注意義務違反的有力證據。因此,公法規範標準成為判斷私法上注意義務具體內容時的客觀指標。所以,企業在選擇倉庫時應進行的首要風險管理不僅僅是審查合同條款,還應確認該倉庫是否根據日本倉庫業法合法登記,以及是否被認定為適合自家產品的倉庫類型。這種公法上的確認工作是為了將來確保私法上權利的基礎,可以說是基本的盡職調查。
在日本商法下的仓储经营者与寄托合同
为了理解日本商法中的仓储经营,首先需要准确把握其核心概念:“仓储经营者”和“经营性寄托”。
日本商法第599条将“仓储经营者”定义为“以为他人保管物品于仓库为业的人”。这里关键的是“以为业”,指的是反复持续提供保管服务并由此获利的经营者。仓储经营者在接受客户物品保管时所签订的合同即为经营性寄托合同。
经营性寄托与日本民法所规定的一般寄托合同在法律性质上,特别是在承寄人(保管物品的人)所承担的注意义务水平上,有决定性的差异。在日本民法中,寄托合同原则上是无偿的(不接受报酬),在这种情况下,承寄人的注意义务仅需“与对待自己财产相同的注意”即可。而更高级别的“善良管理者的注意义务”(善管注意义务)仅限于接受报酬的有偿寄托。
相对地,日本商法对商人即仓储经营者进行的寄托,适用更为严格的规则。日本商法第595条规定:“商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接受寄托时,即使不接受报酬,也必须以善良管理者的注意保管寄托物”。这基于一个理念,即仓储经营者作为专业人士保管他人物品,无论是否有对价,都应承担作为职业人所期待的高度注意义务。根据这一规定,即使在特殊情况下保管费用是无偿的,寄托人也能够得到比日本民法上的寄托更为周到的保护。
为了明确这种差异,下表对两者进行了比较。
| 项目 | 民法上的寄托 | 商法上的经营性寄托 |
| 适用法规 | 日本民法 | 日本商法(民法也补充适用) |
| 适用场景 | 包括非商人在内的一般个人、法人间的保管 | 仓储经营者作为业务保管物品的情况 |
| 承寄人的注意义务(无偿的情况) | 与对待自己财产相同的注意义务 | 善良管理者的注意义务(善管注意义务) |
| 报酬请求权 | 除非有特约,否则不能请求报酬(原则无偿) | 即使没有特约,也可以请求相当的报酬(原则有偿) |
如表所示,企业将自己的产品或商品寄存于仓储经营者,这一行为自动进入日本商法的规范之下,为寄托人形成了有利的法律环境。认识到这一点,是构建与仓储经营者关系时的基本前提。
日本倉儲業者的最重要义务:善管注意义务下的寄存物品保管
在倉儲業者根据寄存合同所承担的众多义务中,最为核心且重要的是以善良管理者的注意力保管寄存物品的义务,即“善管注意义务”。
这一善管注意义务源于日本民法(日本民法第400条)的概念,并适用于各种合同类型中的受托人义务。根据日本商法(日本商法第595条),倉儲業者也需遵守此义务。具体而言,倉儲業者必须根据其职业或社会地位,支付交易中通常要求的注意力水平来管理寄存物品。这不仅仅是“像对待自己的物品一样珍惜”,而是作为保管专业人士,需要根据寄存物品的性质和特点维持最佳环境,并采取所有合理措施以防止丢失、损坏或品质下降。
关于善管注意义务的履行,日本商法为寄存人设定了极为有利的规定,即证明责任的转移。日本商法第610条规定:“倉儲業者未能证明其在保管寄存物品时已尽到注意义务,将无法免除因物品丢失或损坏而承担的赔偿责任。”
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通常的合同违反相关诉讼中,受损方(原告,本案中为寄存人)必须具体证明对方(被告,倉儲業者)存在合同违反,即注意义务违反(过失)。然而,对于外部的寄存人来说,了解倉儲中发生的具体细节并收集证据以进行证明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有信息都倾向于倉儲業者一方。日本商法第610条正是为了纠正这种信息不对称,故意将证明责任的规则逆转。
根据这一规则,寄存人在诉讼中只需主张并证明“物品在健全状态下被寄存”以及“物品在损坏状态下被返还(或未被返还)”即可。之后,除非倉儲業者积极证明“我们作为专业人士已尽到一切应尽的注意义务,没有疏忽”,否则无法免责。这对倉儲業者来说是一个极高的门槛,结果是寄存人的权利得到了强有力的保护。这种法律机制为倉儲業者提供了强烈的动机,以维持高标准的运营,并在可能发生的情况下详细记录管理状况。
通过实际的裁判例,我们可以更具体地理解这一严格注意义务的内容。
例如,在2017年发生并持续约两周才被扑灭的“Askul倉庫火災”诉讼中,东京地方法院在2023年4月26日指出,进出倉庫的业者使用叉车不当可能是火灾原因,并在提到倉庫方的管理体系时,最终判决业者方支付约51亿日元的赔偿。在此事件中,尽管火灾报警器已启动,但员工误判为误操作并将其停止,这一事实也被揭露,这表明注意义务不仅限于设备的维护,还包括建立和遵守紧急情况下的适当应对程序。
还有一些案例中,根据寄存物品的特性要求特别的注意义务。在2012年6月7日,札幌地方法院的判决中,一家接受葡萄酒寄存的倉儲業者未能维持合同规定的温度(约14度)和湿度(约75%),被认定为疏忽。在这个案例中,尽管葡萄酒本身没有物理损坏,但法院判定未能提供合同规定的保管环境本身就构成违约,并命令倉儲業者赔偿寄存人支付的全部保管费用。同样,对于需要温度控制的冷冻鲔鱼等物品的保管,倉儲業者也需要具备维持品质所需的高级专业知识和设备管理能力,一旦疏忽,就会立即被追究责任。
这些案例清晰地表明,倉儲業者的善管注意义务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各个合同内容、寄存物品的性质以及业者所属行业的专业标准,具体化为动态的义务。
仓库收据:支撑物品流通与金融的有价证券
在寄存合同中,寄存人可以要求仓库经营者发行证明所寄存物品的“仓货证券”。根据日本商法(日本商法)第600条,如果寄存人提出要求,仓库经营者有义务交付仓货证券。这种仓货证券不仅仅是一张寄存凭证,它是由日本商法赋予特别法律效力的“有价证券”,在物品流通和金融领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首先,并非所有的仓库经营者都能发行仓货证券。根据日本仓库业法(日本仓库业法)第13条,只有获得国土交通大臣特别许可的、被认为具有信用力和业务执行能力的经营者才被允许发行。这个许可制度是保障仓货证券信用性的第一道门槛。根据日本商法规定,发行的证券必须记载寄存物的种类、品质、数量、寄存人的姓名或商号、保管地点、保管费等法定事项。
仓货证券最强大的法律效力在于其流通性,即通过背书可以转让的可能性。仓货证券可以像汇票或支票一样,通过在证券背面记载转让意愿并签名的“背书”这种简易方式,连续转让给其他人。
背书转让带来的第一个效果是“物权效力”。转让仓货证券等同于转让在仓库中保管的物品本身的所有权,具有相同的法律效果。这使得企业可以在不需要物理移动笨重或体积庞大的商品的情况下,仅通过移动一张纸质的证券来买卖或转移所有权。这在国际贸易或国内大宗交易中,极大地促进了交易的快速化和成本削减。
第二个效果是“善意持有人”的保护。通过正当背书且在不知道证券取得原因有瑕疵的情况下(善意)取得仓货证券的人,即使前一个转让者没有正当权利,也能完全取得证券记载的权利。此外,日本商法第604条规定,仓库经营者不能以仓货证券记载与事实不符来对抗善意持有人。例如,仓库经营者虽然收存了A商品,却错误地在证券上记载收存了更高品质的“A+”商品,那么善意取得该证券的人,仓库经营者不能以“实际商品是A”为由拒绝交付,而必须交付“A+”或赔偿差额。这一规定确保了对证券记载内容的绝对信任,并提高了证券的流通性。
这些法律效力的结合使得仓货证券从单纯的物品兑换券升华为具有金融价值的资产。企业可以在不移动仓库中存货的情况下,将体现存货的仓货证券带到银行,作为融资的担保(供应链金融)。银行通过接受证券的背书转让,获得对物品的确切担保权,并作为善意持有人受到保护,因此可以放心地执行贷款。这样,物理上固定的存货(库存)通过仓货证券这一媒介转变为流动的金融资产(流动资金)。对于在日本开展业务的外国企业来说,理解并利用这一仓货证券制度,不仅可以提高库存管理效率,还可以多样化运营资金的筹集手段,优化资本效率,成为重要的战略。
日本倉儲業者的權利:為保管費等設置留置權
倉儲經營者在對寄託者承擔各種義務的同時,也擁有為了確保自身債權的強大權利。其中的代表就是在日本商法中規定的「商事留置權」。
留置權是指占有他人物品的人,在收到與該物品相關的債權償還之前,可以拒絕交付該物品的權利。倉儲經營者可以為了確保未支付的保管費、裝卸費、垫付款等債權,留置寄託者交付的物品,拒絕返還。
極其重要的是,日本商法所定義的商事留置權,其成立條件比日本民法所定義的一般留置權(民事留置權)要寬鬆得多。民事留置權的成立需要「債權與留置物之間有直接的關聯性」。例如,如果一個手錶的修理費未付,修理業者可以留置該手錶,但不能留置客戶偶然忘記的與之無關的包包。
然而,在商人之間(事業者之間)的交易中適用的商事留置權,則不需要這種關聯性要求。也就是說,如果債權人(倉儲經營者)和債務人(寄託者)都是商人,且該債權源於他們的商業交易,即使留置的物品與債權沒有直接關聯,也可以行使留置權。
這一差異帶來的實踐後果是巨大的。例如,假設某企業將A、B、C三批不同的商品寄存於同一倉儲經營者。該企業對於A批商品的保管費發票內容提出疑問,暫時保留支付。在這種情況下,倉儲經營者當然可以留置A批商品以收回未付的保管費。但是,商事留置權的效力不止於此。倉儲經營者為了確保A批商品相關債權,甚至可以合法地留置已經完全支付保管費的B批和C批商品,拒絕交付。
這條規則對倉儲經營者來說是一種極為強大的債權回收手段,但對寄託者來說可能是一個意想不到的風險。一個小的請求爭議可能會導致所有存放在該倉儲經營者處的庫存出貨停止,進而癱瘓整個供應鏈。這給倉儲經營者在爭議中提供了巨大的談判優勢。因此,日本使用倉儲服務的企業必須時刻記住商事留置權的廣泛效力,準確且及時地管理和支付發票,這對於業務連續性來說至關重要。法務和財務部門必須深刻認識到,對於部分請求的輕率支付保留可能會對整個業務造成嚴重影響。
关于寄存物品的返还与寄存合同的终止
寄存合同的主要目的在于寄存物品的返还,并以此达成合同的终止。理解合同终止阶段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特别需要注意的法律期限,对于顺利完成交易至关重要。
寄存人或正当持有仓储凭证的人,原则上有权随时要求返还寄存物品。根据日本民法的规定,即使双方约定了保管期限,寄存人也可以在期限届满前要求返还 。但是,如果期限前的返还请求给仓库经营者造成了损害(例如,基于长期合同提供了折扣保管费),寄存人可能需要承担赔偿损害的义务 。
为了接收寄存物品的返还,通常需要遵循仓库经营者设定的条款(如标准仓储寄存条款)中规定的程序(出库程序)。如果发行了仓储凭证,那么提交该凭证是返还的条件 。如果没有发行凭证,则需要提交仓库经营者指定的书面文件等来要求出库。
寄存合同的终止原因通常是寄存物品的全部返还,但除此之外,合同期限的届满或任一当事人的合同解除也会导致合同终止。仓库经营者在寄存物品不再适合保管或可能对其他寄存物品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可以解除合同 。同样,寄存人也可以按照合同规定的程序(例如,提前一定期限的解约预告通知)中途解除合同 。
在合同终止过程中,寄存人最需要注意的是与损害赔偿权相关的“短期消灭时效”。日本商法规定,对于仓库经营者的责任,相比一般债权的消灭时效(原则上为5年),设定了更短的1年期限。具体来说,关于寄存物品的灭失或损坏,对仓库经营者的损害赔偿权,原则上如果在物品从仓库出库之日起1年内未行使,则因时效消灭 。如果寄存物品全部灭失,则从仓库经营者向寄存人发出灭失通知之日起1年。这个短期时效的目的是为了尽快稳定商业交易的法律关系,但对寄存人来说,这是一个可能导致权利丧失的重要期限。
这个短暂的1年期限在实务中往往被忽视,成为“程序上的陷阱”。企业从仓库提取大量物品时,并不一定会立即进行全面的详细检查。物品可能直接被送往其他流通点,或者直到销售前都保持包装状态。几个月后,当企业准备使用或销售产品时,才首次发现损坏、数量不足或品质退化等问题。然而,如果此时已经过了出库日起的1年期限,即使仓库经营者的责任很明显,法律上也已无权要求赔偿。
为了避免这种风险,企业需要法务部门与物流、库存管理部门协作,建立内部规程。具体来说,从日本仓库提取物品后,需要尽可能迅速且彻底地实施检查流程。如果发现任何异常,应立即通知仓库经营者,并在1年的时效期限届满前,完成谈判或提起诉讼等法律权利行使的准备。这个短期消灭时效的存在不仅是法律知识,更是规定了企业具体业务流程和内部控制方式的极其实践性的规则。
总结
正如本文所详述,日本的商法及仓储业法所规定的仓储业务的法律框架,是精细且多层次构建的。企业在日本使用仓储服务时,为确保其资产和权利得到保护,必须始终注意几个重要的法律检查点。首先,在合同谈判前,确认交易对方的仓库是否根据日本的仓储业法合法注册。其次,理解仓储业者所承担的“善管注意义务”这一高度的注意义务,以及在损害发生时证明责任的转移,这对寄托人来说是有利的规则。第三,战略性地利用具有超越普通保管证的价值的“仓货证券”的流通性和金融功能。第四,认识到仓储业者拥有的强大的“商事留置权”可能对自家供应链带来的潜在风险,并进行适当的支付管理。最后,为了不失去损害赔偿请求权,遵守“1年”这一极短的消灭时效期限,建立严格的检品体系。掌握这些要点是确保日本顺畅物流和可靠风险管理的关键。
我们Monolith法律事务所在本文解释的商事寄托和仓储业务相关法务方面,代表国内外众多客户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我们事务所不仅拥有精通日本法律制度的律师,还有多名持有外国律师资格的英语律师。这使我们能够为在国际业务中面临特殊挑战的企业提供细致的法律支持,克服语言和文化障碍,确保顺畅的沟通。从合同的起草与审查到与仓储业者的谈判,再到万一发生争议时的诉讼应对,我们提供全面的法律服务,保护贵公司在日本的业务和资产。
Category: General Corpor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