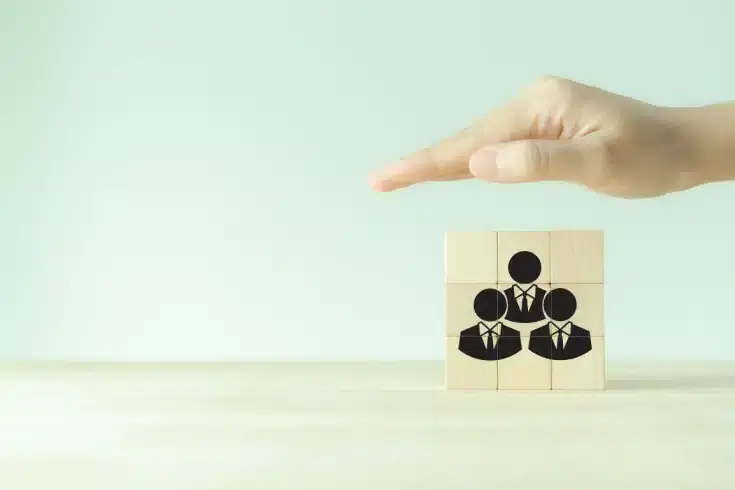日本勞動法中判斷勞動者性質的標準:關於適用範圍的司法途徑解說

日本的勞動法制對「勞動者」提供了厚實的保護。然而,誰能夠被認定為「勞動者」,這個問題並非僅憑契約的名稱或當事人的意圖就能決定。日本的法院在判斷「勞動者性」時,不會僅依據契約的形式,而是根據工作的實際情況。如果這一判斷出錯,企業可能會面臨意料之外的法律風險。例如,若原本簽訂業務委託契約的個人,後來被法院認定為勞動者,企業可能會被要求追溯支付加班費和社會保險費。這不僅僅是金錢上的負擔,勞動者性的認定對於依賴自由職業者或個體經營者等靈活勞動力的企業商業模式,可能是一個影響深遠的經營風險。因為一旦被認定為勞動者,就會適用日本勞動基準法規定的關於工作時間、休息和休假的嚴格規定。本文將從日本勞動基準法中「勞動者」的定義出發,詳細解說法院在判斷「勞動者性」時所依據的標準,並結合豐富的具體案例,闡述這一司法框架。這個問題不僅是企業合規的挑戰,更是與企業持續發展相關的戰略性課題。
在日本勞動法下「勞動者」的法律定義
在日本的勞動法體系中,「勞動者」的定義根據其所依據的法律而有細微差異。理解這些差異對於準確把握風險至關重要。
首先,日本勞動基準法規定了個別勞動者的勞動條件最低標準,其第9條將「勞動者」定義為「不問職業種類,被事業或辦公所使用,並獲得報酬的人」。這一定義是許多個別勞動法中共通使用的核心概念,例如旨在保障勞動者安全與健康的日本勞動安全衛生法,以及保障最低工資的日本最低工資法等。同樣地,日本勞動契約法第2條也採用了與勞動基準法幾乎相同的定義,界定了個別勞動契約關係中的基本保護對象。
相對地,保障勞動者團結權和集體談判權的日本勞動組合法則包含了更廣泛範圍的保護對象。該法第3條將「勞動者」定義為「不問職業種類,以工資、薪水或其他類似收入為生活來源的人」。這一定義並未包含勞動基準法中的「被使用者」要求,而是更廣泛地針對經濟上依賴他人提供勞務的人。
這些定義上的差異會帶來重要的法律後果。即使某人被判定不符合勞動基準法上的「勞動者」資格,因而無法獲得加班費賠償,他們仍可能符合勞動組合法中更廣義的「勞動者」定義。在這種情況下,該個人將有權組建勞動組合,並要求企業進行集體談判。因此,企業不僅要考慮勞動基準法上的風險,還要考慮勞動組合法上的風險,需要從雙重視角進行勞務管理。
勞動者性判斷的司法框架:重視實質而非形式的方法
即使契約書明確寫明「業務委託契約」或「承攬契約」,也並不意味著就此否定勞動者性質。日本的法院採取一貫立場,不拘泥於契約的名稱等形式要素,而是基於當事人間的實質關係,即勞務提供的實際情況來判斷勞動者性質。這種「實質重視」的方法對於防止地位強勢的使用者濫用契約形式,不當逃避勞動法上的保護,是一項不可或缺的原則。
這一判斷框架的基礎是1985年(昭和60年)前勞動省研究會公布的「勞動基準法研究會報告」(以下簡稱「昭和60年報告」)。雖然這份報告不是法律本身,但對後續的判例和行政解釋產生了巨大影響,至今仍作為判斷勞動者性質的事實上的指南。
昭和60年報告將判斷標準分為兩個層次進行整理。首先是判斷核心的「使用從屬性」標準,這是對勞動基準法第9條「被使用者,並獲支付薪資者」的具體化,由「指揮監督下的勞動」和「報酬的勞務對價性」兩個方面構成。其次,當這些主要標準無法輕易判斷時,還有補充性要素來加強判斷。這一穩定的解釋框架長期維持,暗示了日本法制度傾向於重視判例積累而非頻繁法律修正的漸進式解釋發展。因此,理解這份歷史性報告的內容,對於預測當代勞動爭議中法院的判斷至關重要。
判斷的核心標準:日本「使用從屬性」的具體要素
「使用從屬性」是判斷勞動者性質時最為關鍵的概念。它涉及是否存在一種從屬關係,即勞動者在他人的指揮監督下提供勞務,並因此獲得報酬。日本的法院會綜合考慮以下多個要素,以判斷是否具有使用從屬性。
在日本指揮監督下的勞動
「在日本指揮監督下的勞動」並不僅僅意味著接受工作指示。在這方面,指示的具體性、強制力程度以及工作執行中的裁量範圍等多方面因素都會被綜合考量。
對工作請求・指示的接受與否自由
即使契約書中形式上記載了拒絕工作請求的自由,如果實際上無法拒絕,則這種情況會被認為是肯定指揮監督關係的。例如,如果一旦拒絕請求,之後的工作量顯著減少,或者完全沒有工作,這種不利益將導致所謂的「自由」僅是名義上的。在判例中,如果根據排班表工作並且無故缺勤會被罰款,則認為沒有接受與否的自由,從而強烈認定勞動者性質(東京高等裁判所2018年(平成30年)10月17日判決)。另一方面,如果司機可以自由選擇「上班」「聯絡(可對應)」「休息」,即使拒絕工作也沒有懲罰,則接受與否的自由被認可,並被視為否定勞動者性質的一個因素(大阪地方裁判所2020年(令和2年)12月11日判決)。
關於工作執行的指揮監督
在工作執行方法上接受了多麼具體的指示和管理,也是一個重要的判斷因素。不僅僅是工作目的或截止日期的指示,如果連過程和手段都有詳細的指示,則指揮監督關係會更加明顯。例如,在一個語言學校的講師被強制使用學校指定的教材和手冊,並且被強制參加定期培訓的案例中,認定了強烈的指揮監督(名古屋高等裁判所2020年(令和2年)10月23日判決)。另一方面,對於大學的兼職講師,除了講義大綱外,具體的授課內容的制定被委託給講師的廣泛裁量,這種情況被認為指揮監督關係較弱(東京地方裁判所2022年(令和4年)3月28日判決)。
時間性・場所性的約束
被指定工作地點和時間,以及雇主對出勤的管理,是指揮監督關係的典型跡象。打卡義務、嚴格的班次管理、提交詳細的工作日報等,都會增強時間性和場所性的約束。即使是在家工作這樣的形式,如果管理了登入和登出時間,或者要求始終在線,則實質上被管理了工作時間,也可能被認為存在約束。在一個遊戲程序員被要求使用公司設施並在公司內工作,並被指示打卡的案例中,認定了強烈的約束性,並與肯定勞動者性質相關(東京地方裁判所1997年(平成9年)9月26日判決,タオヒューマンシステムズ事件)。
勞務提供的替代性
勞務提供是否可以由本人的裁量讓第三者代替,也是一個判斷因素。如果本人可以自費和自負責任地使用助手或替代者,則這表明了作為業主的特徵,並會削弱勞動者性質。相反,如果無論出於何種理由都嚴格要求本人提供勞務,則這表明了高度的屬人性勞務,即具有勞動契約的性質,並增強了勞動者性質。這種替代性本身不是決定性因素,但在判斷指揮監督關係的存在與否時,它起到了補充作用。
報酬與勞務對價性在日本的法律下
報酬是否具有對於所提供勞務本身的對價(即工資)性質,是一個需要評估的問題。報酬的性質不是根據其名稱來判斷,而是應從計算方法和支付方式等實際情況來確定。
當報酬以時薪、日薪、月薪等形式支付,並且根據工作時間的長短來決定時,本所通常認為它具有「工資」的性質。此外,如果報酬根據缺勤的天數或時間減少(所謂的「無工作無報酬」原則適用),或者對於加班支付額外津貼,這些情況也強烈暗示了報酬的勞務對價性。在一個稅理士的案例中,無論業務量多少,每月都支付固定金額,並且還發放了獎金,因此報酬被認定為在指揮監督下提供勞務的對價(東京地方裁判所2011年(平成23年)3月30日判決)。
相對地,如果報酬完全基於業務成果來決定,例如根據銷售額的純佣金制或者在項目完成時一次性支付的承包費用,這種形式更強烈地表現出作為業者間交易的對價性質,並減弱了勞動者性質。然而,即使表面上是佣金制,如果設有最低保障薪資等包含生活保障性質的元素,則可能會被考慮為肯定勞動者性質的因素。
判斷勞動者性質的補充要素
即使考慮了與「使用從屬性」相關的核心要素,有時仍難以明確判斷勞動者的存在。在這些邊界案例中,法院會考慮以下補充要素,進行綜合判斷。
事業者性質的有無
勞務提供者是否具有獨立事業者的特徵,是一個特別重要的補充判斷要素。這是從勞務提供者是否自行承擔計算和風險來經營事業的角度進行評估的。
具體的判斷材料包括,首先,勞務提供者是否自費擁有或承擔對完成工作不可或缺的機械、器具、車輛等。例如,如果擁有昂貴的卡車或重型機械,這強烈暗示了其作為事業者的性質。其次,報酬金額是否顯著高於從事相同工作的企業正職員工的薪資也會被考慮。這種高額報酬被解釋為包含了作為事業者所承擔的經費和商業風險的對價,是削弱勞動者性質的因素。此外,勞務提供者是否自行承擔業務上的損害責任,或是否使用獨立的商號進行營業活動等,也是判斷事業者性質時會考慮的因素。
專屬性的程度
如果對特定企業的經濟依賴度很高,這可能成為增強勞動者性質的一個因素。專屬性的程度從兩個方面進行評估。一是合約上是否禁止從事其他公司的業務,或者從時間上和物理上實際上難以兼顧。如果被特定企業的工作大量佔用時間,結果無法從事其他工作,則專屬性被認為是高的。另一方面是報酬的生活保障性。如果大部分收入依賴於特定企業的報酬,則經濟依賴性被認為是高的,這會增強勞動者性質。
其他要素
除了上述要素,雙方對勞務提供者的認識如何,這一客觀情況也會被考慮。具體來說,是否從報酬中進行了薪資所得的源泉扣繳,是否讓勞務提供者加入勞動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和社會保險(健康保險、厚生年金保險),是否適用企業的就業規則等。這些事實表明企業方面將該個人視為勞動者,是支持肯定勞動者性質判斷的補充材料。
根據日本最高法院判例指引:橫濱南勞基署長事件
作為判斷勞動者性質的標準案例,日本最高法院於1996年11月28日(平成8年)作出的判決(橫濱南勞基署長事件)提供了極其重要的指引。
該案件涉及一名駕駛員,他使用自己所有的卡車主要從事於一家造紙公司的產品運輸工作,在工作中受傷後申請勞動者災害補償保險給付。然而,勞動基準監督署長認為該駕駛員不符合「勞動者」的資格,因此不予支付,駕駛員隨後提起訴訟,要求撤銷該不支給決定。
最高法院最終否定了該駕駛員的勞動者性質。其判斷過程具體應用了之前提到的判斷框架,充滿啟示意義。
首先,最高法院審查了公司的指示內容,認為關於運輸物品、運輸目的地、交貨時間等指示,鑑於運輸業務的性質,作為訂單方是必要的正常指示,不能因此認為存在具體的指揮監督。
其次,就時間和場所的約束性而言,最高法院指出,駕駛員在完成一次運輸任務後就脫離了公司的管理,直到接到下一個任務指示前都可以自由支配時間,與公司的一般員工相比,其受到的約束程度要寬鬆得多,不足以認定其處於指揮監督之下。
最高法院特別重視的是「事業者性」的要素。駕駛員自己擁有價值不菲的卡車,並自行承擔油費、維修費、保險費等經費。此外,其報酬是根據運輸量來支付的,並未進行薪資所得的預扣稅。基於這些事實,最高法院認定駕駛員作為獨立的事業者,在自己的風險和計算下從事運輸業務,因此否定了其勞動者性質。
該判決明確指出,判斷勞動者性質不應僅依賴特定要素,而應綜合考量指揮監督關係、約束性、報酬性質以及事業者性等多個要素。特別是當勞務提供者具有明顯的事業者性時,這可能成為否定勞動者性質的有力因素,因此這是一個劃時代的判例。
適用於現代就業形態:日本Gig工作者的勞動者性質
透過平台承接臨時工作的「Gig工作者」的出現,對傳統的勞動者性質判斷框架提出了新的問題。特別是,像食品外送服務的外送員等工作方式,已成為全球性的討論焦點。
在日本,Uber Eats的外送員組成的勞工組合向經營公司提出團體談判要求,但公司方面否認外送員的勞動者性質並拒絕談判,這一問題引起了爭議。在這起事件中,東京都勞動委員會於2022年判斷外送員符合日本勞動組合法上的「勞動者」定義,並命令公司應對團體談判。這一判斷基於外送員作為平台業務運行不可或缺的勞動力被組織納入、報酬實際上由公司單方面決定、以及透過應用程式實質上接受指揮監督等理由。這是一個象徵性的案例,展示了前述的勞動基準法和勞動組合法中「勞動者」定義的差異如何在具體爭議中顯現。
然而,關於Gig工作者是否能作為勞動基準法上的「勞動者」,從而獲得加班費和最低工資等保護,司法判斷仍未明確,目前仍在期待未來裁判例的積累。在一起外送員因不合理的帳號停用(實質上等同於解僱)提起的損害賠償民事訴訟中,避開了對勞動者性質的正面判斷,而以公司方面支付和解金的方式達成和解的案例也存在。
這些動向顯示,法律面臨的挑戰在於如何將傳統的判斷要素適用於現代的工作方式,例如算法對工作分配和評價系統是否構成「指揮監督」,以及外送員所擁有的自行車或摩托車是否可視為表明「事業者性質」的昂貴機械設備等問題。企業必須認識到,與Gig工作者的合約可能同時包含了勞動組合法上的團體談判風險和將來可能被認定為勞動基準法上的勞動者的風險。
比較表:判斷勞動者性的要素
將迄今為止所解說的勞動者性判斷要素整理起來,如下表所示。請注意,此表僅為指示判斷方向性的簡化版,實際判斷需綜合考慮個別案件中的具體事實關係。
| 判斷要素 | 肯定勞動者性的情況 | 否定勞動者性的情況 |
| 諾否的自由 | 事實上無法拒絕工作的要求,拒絕會帶來不利。 | 可以自由選擇是否接受工作要求,且無任何懲罰。 |
| 業務遂行上的指揮監督 | 接受詳細的工作內容和執行方法指示與管理(例如:操作手冊、定期報告等)。 | 在工作執行方法上有廣泛的自主權(僅指定成果物)。 |
| 時間的・場所的拘束性 | 工作時間和地點被指定,並受到出勤管理(例如:打卡、輪班制等)。 | 無工作時間和地點的拘束,可以根據自己的判斷自由決定。 |
| 代替性 | 必須由本人提供勞動,不允許第三者代替。 | 可以根據自己的判斷和費用使用助手或代替者。 |
| 報酬的性質 | 根據工作時間或勞動提供本身支付報酬,如時薪或固定薪資。有缺勤扣款。 | 根據工作成果支付報酬(例如:純佣金制、按項目計酬)。 |
| 事業者性 | 公司提供機械、器具、材料,並承擔主要費用。 | 自己擁有昂貴的機械、器具,並自行承擔費用(自擔風險和計算)。 |
| 專属性 | 合約上或事實上禁止或限制在其他公司就業。收入依賴單一公司。 | 在其他公司就業自由,並實際上從事兼職。 |
總結
在日本的勞動法中,判斷某個人是否屬於「勞動者」,不是基於契約書的名稱等形式,而是基於勞務提供的實態,綜合考量多角度的要素來決定。這個判斷的核心概念是「使用従屬性」,其中包括指揮監督的有無、時間上和場所上的拘束性、報酬的勞務對價性等具體因素的考量。此外,還會考慮到事業者性或專屬性等補充性要素,並根據個別案例得出結論。這一判斷框架已由最高法院的判例確立,儘管面臨著像零工經濟這樣新型態就業形式帶來的新解釋挑戰,其基本結構仍然被保持。對於企業經營者和法務負責人來說,準確理解這一複雜且變動的法律概念,並不斷檢視公司的勞務管理體系,對於避免意外的法律和財務風險,實現持續性的事業經營至關重要。
モノリス法律事務所針對日本國內眾多客戶,在本文所討論的勞動者性判斷相關的法律問題上,擁有豐富的諮詢經驗。本所事務所擁有多名具有外國律師資格的英語使用者,能夠從國際視角出發,為日本複雜的勞動法體系提供無縫的法律支持。無論是勞動力的分類評估、契約書的起草與審查,還是相關爭議的代理業務,本所都能提供符合貴公司需求的專業服務。
Category: General Corpor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