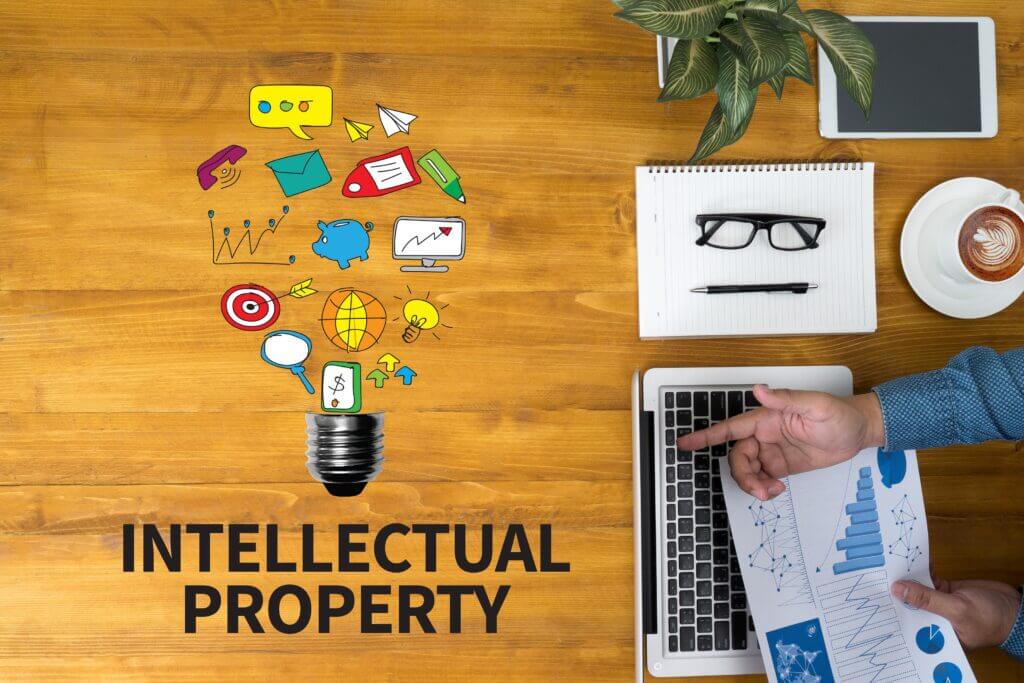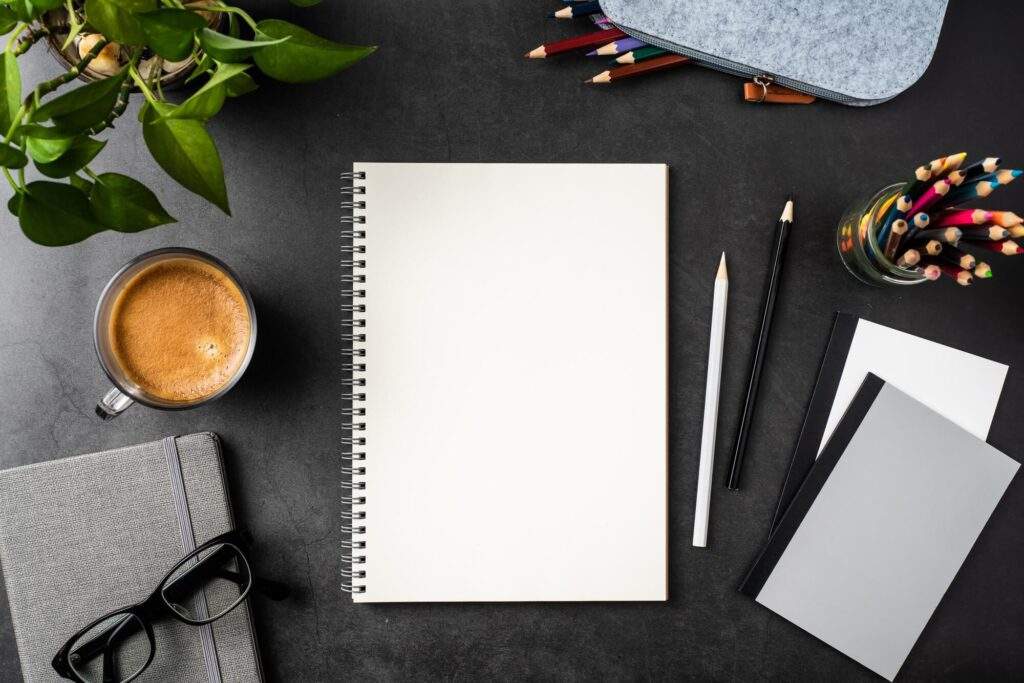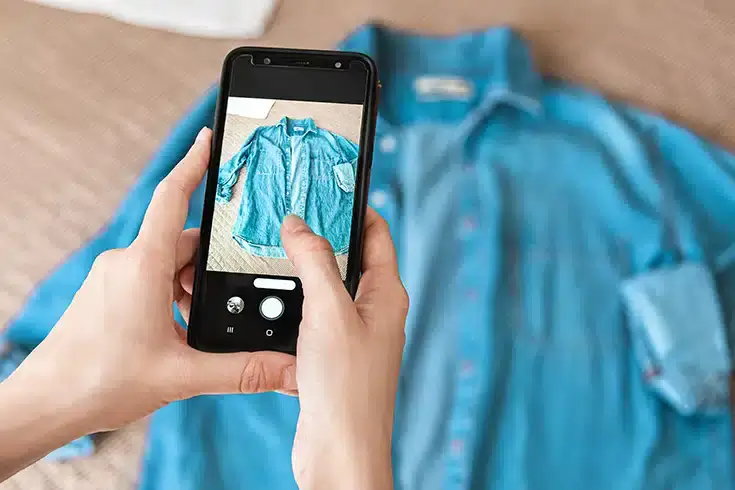在日本勞動法中透過法院進行的爭議解決程序:作為經營策略的理解

在企業經營中,與勞工的爭議是不可避免的經營風險之一。然而,這些爭議不僅僅是法律問題,解決過程本身對企業的財務、聲譽以及組織文化都會產生深遠的戰略影響。當爭議發生時,企業選擇哪種解決程序,將極大地影響成本、時間,以及最終結果,這是一項至關重要的經營決策。日本的司法制度為解決勞動關係的爭議提供了多種具有不同特點和戰略意義的程序。具體來說,有追求迅速解決的「勞動審判程序」、深入爭議權利關係的「民事通常訴訟」、爭議初期的緊急應對「保全訴訟」,以及專注於金錢請求的「少額訴訟」和「民事調解」。這些程序不僅僅是選擇列表,而應根據情況作為戰略性工具來使用。本文旨在從經營者的視角深入分析這些司法程序的特性,提供實踐指南以最大化企業利益並最小化損害。理解每個程序的法律機制,以及背後的力學、風險和機會,將是有效管理爭議危機的第一步。
勞動審判手續:重視迅速性的實踐解決方案
日本勞動審判的性質
日本的勞動審判手續是一種專門的司法程序,旨在迅速且切合實際情況解決個別勞動者與事業主之間發生的民事爭議,如解雇的有效性或未支付工資的支付問題。該程序最大的特點在於其審理結構。審理由一名職業裁判官即勞動審判官和兩名具有勞動關係專業知識與經驗的勞動審判員組成的「勞動審判委員會」進行。這種三人組成的機制不僅純粹從法律角度進行判斷,還融入了勞資慣行和現場實況等實踐視角,明確展現了該程序追求的不僅僅是形式上的權利義務確定,而是現實中合理且適當的解決方案。
從公司角度看的程序流程
對企業而言,日本的勞動審判程序進展極為迅速,初期應對將大幅影響後續發展。
首先,企業通常是在收到法院發送的「傳票」以及勞動者陳述主張的「申請書」時,才首次得知紛爭已轉入法律程序。從收到通知到第一次開庭,原則上只有不超過40天的極短時間。
在這有限的時間內,企業必須撰寫詳細的「答辯書」來反駁勞動者的主張,並且要在審判所定的期限前,連同支持證據一起提交給法院。面對勞動者花時間準備的申請,企業方必須在幾週的壓倒性短時間內構建反駁,這時間的限制成為企業面臨的最大挑戰。
第一次開庭不僅僅是程序性的確認,勞動審判委員會會在此期間對企業的代表或管理層等相關人員進行直接而集中的質詢,以整理爭點。在許多情況下,委員會會在這第一次開庭形成對事件的整體認識和初步評價(心證),這將對後續的調解談判產生巨大影響。如果準備不足就參加第一次開庭,將極難扭轉不利局面。
勞動審判程序原則上旨在3次開庭內結束審理。程序的重點放在當事人間通過協商達成解決方案,即「調解」的成立。實際上,約70%的勞動審判案件都是通過調解解決的。只有在調解未達成時,勞動審判委員會才會根據案件的實際情況作出判斷,即「審判」。然而,如果任何一方當事人在收到通知之日起2週內提出異議,審判將失去效力,程序自動轉入民事常規訴訟。
經營上的戰略意涵
在日本,勞動審判手續對企業而言,既有明顯的優勢,也同時攜帶著同等重大的風險。
優勢方面,首先是其迅速性。平均審理期間約為3個月(80至90天),與可能持續超過一年的民事訴訟相比,能夠將企業資源(時間、費用、人力資源)的浪費降至最低。其次,由於手續是非公開的,因此在保護企業聲譽、防止對其他員工造成動搖以及避免媒體報導等次生損害方面極為有效。第三,由於向法院支付的手續費相對於訴訟來說較低,且審理期間短,因此有可能抑制包括律師費用在內的總成本。
然而,風險也是嚴重的。最大的缺點,如前所述,是準備期間極短。這可能導致企業在未能充分準備防禦的情況下,被置於不利的立場。此外,由於整個手續強烈傾向於透過調解解決問題,因此可能會受到委員會不利的心証影響,即使在法律上有正當主張,也可能會面臨不得不接受包含一定讓步的和解的強大壓力。再者,由於日本勞動法制本質上對勞動者保護較為厚重,且勞動審判更重視基於實際情況的解決而非嚴格的法律解釋,結果往往對企業方不利。
應該理解,這種手續雖然採取司法手續的形式,但實際上是在擁有強大權威的勞動審判委員會下進行的,極為高壓的談判場合。企業的目標不是在法庭上「勝訴」,而是利用法律主張作為談判的武器,盡可能在調解中達成有利條件。因此,最初提交的答辯書不僅是法律文件,更是在這場短期決戰的談判中極為重要的開場陳述。
此外,手續的非公開性雖然在保護企業聲譽方面有很大的優勢,但從戰略角度來看,需要謹慎對待。勞動者方可能會察覺到企業希望避免公開法庭的爭議,並將其作為談判的槓桿。換句話說,他們可能會施加一種無言的壓力:「如果不滿足本所的要求,本所將提出異議,將案件轉移到公開訴訟中。」因此,企業戰略應該是在勞動審判的框架內結束爭端。為此,從手續的初期階段開始,就必須提出有說服力的主張和證據,向委員會和對方雙方展示即使轉入訴訟階段也能充分應戰的姿態,讓他們認識到「在此階段達成合理解決比轉入訴訟更為明智」。
日本民事通常訴訟:權利關係的最終爭議手段
日本民事通常訴訟的性質
在日本,當其他程序如勞動審判無法解決問題,或案件性質上一開始就需要法庭嚴格判斷時,民事通常訴訟便是被選擇的傳統且正式的裁判程序。若對勞動審判的裁決提出異議,程序便會自動轉入民事通常訴訟。此程序的特點是,雙方當事人透過稱為「準備書面」的文件反覆陳述法律主張,並基於證據嚴密證明各自主張的正當性,形成一種對審結構。其目的不在於尋求符合實際情況的靈活解決方案,而是旨在確定基於法律和證據的權利義務關係。
程序與審理期間
訴訟程序在日本始於原告(通常為勞工)根據請求金額向地方法院或簡易裁判所提交「訴狀」。隨後,雙方當事人將進行數月,有時甚至超過一年的時間,進行多輪的準備書面交換。法院的期日主要是定期召開,以確認提交的書面內容並協商下一步準備工作。
當事實關係存在爭議時,與勞動審判不同,會通過正式的「證人詢問」程序,直接聽取當事人本人或相關人員的陳述,並檢驗證據。這一證人詢問階段是影響判決走向的重要時刻。
審理結束後,法院將作出「判決」。日本的司法制度採用三審制,對於不服第一審判決的當事人,可以向高等法院「控訴」,進而向最高法院「上訴」。因此,獲得最終確定判決可能需要數年時間。然而,在訴訟的任何階段,都可以通過法官的仲介達成「訴訟上的和解」來解決爭端,在實務上,許多案件也是通過和解而結束。
經營上的戰略意涵
民事通常訴訟在日本,對企業而言,與勞動審判具有截然相反的特性。
其最大的優勢在於能夠充分確保準備期間。長期的審理期間為企業提供了充足的時間來策劃精密的法律防禦戰略、收集廣泛的證據,並充分展現自己的主張。此外,由於審理基於嚴格的法律解釋和判例進行,若企業方有法律上強有力的依據,則獲得有利判決的可能性大增。
然而,其缺點極為嚴重。首先,解決問題所需的時間非常長。僅第一審就平均需要超過一年的審理期間,若進行控訴審、上訴審,紛爭的最終解決可能要數年之後。這將長期占用經營層的時間和注意力,對企業來說是一大負擔。其次,成本極高。隨著審理期間的延長,律師費用也會急劇增加。第三,且對經營層來說最重要的是,訴訟原則上是公開的。這可能導致紛爭內容公之於眾,被媒體報導,從而對企業的品牌形象和社會信譽造成重大損害。同時,對內部而言,也可能給其他員工帶來不安和不信任,對整個組織的士氣產生負面影響。最後,由於訴訟本質上是徹底的爭鬥,當事人間的對立可能變得不可調和,即使勞工勝訴並復職,之後建立良好的雇傭關係幾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日本,民事通常訴訟往往是在之前的談判或勞動審判等紛爭解決嘗試失敗後,作為最後手段被選擇。其高昂的成本、長期的時間消耗以及公開帶來的聲譽風險,對雙方都不是吸引人的選擇。這種手續對企業的戰略價值,不必然在於「勝訴」,而更在於展現出「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戰鬥到底」的堅定態度。這種可信的威脅,在非公開的勞動審判階段,可以抑制對方的過高要求,並在更現實的賠償金水平上達成和解,成為強有力的談判籌碼。那些顯示出無論如何都要避免訴訟的企業,在談判初期階段就會失去重要的影響力。
在日本的勞動審判與民事通常訴訟的策略性比較
當企業面臨勞動爭議時,選擇進行勞動審判或民事通常訴訟,或是為其中一種程序做準備,從策略性角度理解兩者的根本差異是至關重要的。
最明顯的差異在於解決所需的時間。勞動審判的目標是在原則上3次以內的期日內結束審理,平均約3個月內即可達成解決,這是一個極短的期間。相比之下,民事通常訴訟即使只是第一審,也通常需要1年到2年,甚至更長的時間,紛爭的長期化是不可避免的。
這個時間上的差異也直接影響到費用。勞動審判的法院手續費設定為訴訟費用的大約一半,加上審理期間短,結果律師費用也傾向於比訴訟低。另一方面,民事通常訴訟由於長期化,律師費用可能顯著增加。
在企業的聲譽管理中,程序的公開性至關重要。勞動審判是非公開進行的,因此可以將紛爭存在本身外泄的風險降至最低。相對地,民事通常訴訟根據憲法要求原則上是公開進行的,任何人都可以旁聽。這對企業來說意味著重大的聲譽風險。
審理的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勞動審判以勞動審判委員會進行的直接口頭質詢為中心,通過對話尋求靈活的解決(調解)。而民事通常訴訟則以提交書面主張和證據為中心,是一種更為形式化和嚴格的程序。
判斷紛爭的主體也不同。在勞動審判中,由1名法官和2名具有勞資雙方實務經驗的專家組成的勞動審判委員會作出判斷,而在民事通常訴訟中,則由職業法官單獨負責審理。
最後,對判斷提出不服的機制也不同。對勞動審判的判斷,可以通過簡易的「異議申立」來表達不服,這種情況下會自動轉入民事通常訴訟。對於民事通常訴訟的判決,則設有「控訴」或「上訴」等更為複雜和正式的上訴程序。
以下的比較表總結了這些差異。這個表可以幫助特定紛爭情況下的企業判斷哪種程序更符合其策略目標(例如:迅速且保密的解決,或是原則性的徹底主張)。
| 勞動審判程序 | 民事訴訟 | |
| 解決期間 | 迅速(平均約3個月) | 長期(1年以上) |
| 費用 | 相對較低 | 相對較高 |
| 程序的公開性 | 非公開 | 原則公開 |
| 審理的主體 | 勞動審判委員會(法官1名、專家2名) | 法官 |
| 主要審理方法 | 口頭質詢、對話為中心 | 書面主張・立證為中心 |
| 不服申立 | 異議申立後轉入訴訟 | 控訴・上訴 |
緊急應對:日本紛爭初期的保全訴訟
保全訴訟(臨時處分)的性質
在日本,保全訴訟,尤其是在勞動爭議中常用的「臨時處分」,是一種在等待正式訴訟(本案訴訟)判決期間,為了防止可能發生無法恢復的損害,法院會下達臨時措施的緊急程序。其目的在於紛爭初期階段臨時保護勞動者的權利。在勞動爭議中,通常是被解雇的勞動者為了確保自己的職位和收入而使用此程序。
具體來說,以下兩種類型是典型的例子,而且在多數情況下,這些申請會同時提出:
- 職位保全臨時處分:命令確認勞動者暫時擁有員工的地位。
- 工資預付臨時處分:命令企業在本案訴訟進行期間,繼續支付勞動者的工資。
對企業管理的重大風險
由於保全訴訟的緊急性,程序進展極為迅速。從申請到首次聽證通常只需1至2週,而法院的判決在3個月到半年內作出也不罕見。勞動者要在此程序中獲得法院的判決,必須證明「待保全權利」(例如:基於雇傭合約的工資請求權)的存在,以及「保全的必要性」(例如:若不支付工資,生活將陷入困境等無法恢復的損害)這兩個要求。
對企業來說,最大的風險是,如果工資預付臨時處分被批准,將導致不對稱的金錢負擔。根據法院的命令,企業必須持續支付給未就業的勞動者工資。最重要的是,這些支付由於用於勞動者的生活費,即使企業日後在本案訴訟中勝訴,要求返還這些款項也將變得困難。此外,勞動者在獲得臨時處分命令時,通常會因法院的裁量而無需提供擔保或只需提供少量擔保。這一機制導致企業的金錢損失在紛爭持續期間單方面增加,對企業形成強大的壓力,促使其盡早和解。
企業方的防禦策略
對於被申請保全訴訟的企業而言,最有效的防禦策略是徹底攻擊勞動者方主張的「保全的必要性」。具體來說,就是主張該勞動者即使不獲得工資預付,也不會立即陷入生活困境,並提出客觀證據和情況。
企業應提出的具體反駁點如下:
- 勞動者擁有足夠的儲蓄或資產。
- 存在其他穩定收入來源,如配偶的收入或兼職等。
- 已獲得新工作並確保了收入。
當然,與此同時,主張解雇的合法性等企業措施的合法性,並對勞動者所主張的「待保全權利」的存在提出質疑也是重要的。
這一程序利用時間和金錢壓力作為對企業的武器。它具有將經濟負擔從勞動者轉移到企業的效果,並且這種轉移發生在紛爭的非常初期階段。法院命令支付事實上無法返還的工資,導致企業每月的沉沒成本不斷增加。這徹底改變了談判的動力學。爭議不再僅僅是未來和解金額的問題,而是如何盡快停止當前正在發生的金錢流失,這成為了一個緊迫的經營課題。因此,對這種臨時處分的申請進行迅速而有力的反駁,並在初期階段就駁回它,成為避免長期消耗戰的首要任務。
少額訴訟與民事調解:處理金錢糾紛的簡便選擇
少額訴訟
少額訴訟是一種適用於請求60萬日元以下金額支付的極為簡便且迅速的訴訟程序。這一程序的最大特點在於,原則上在一次期日內結束審理,並當庭宣判。因此,當事人必須在審理期日之前準備好所有主張和證據,並提交法庭。
從經營角度來看,這種程序可能被用於處理例如退職員工提出的少額未付工資請求等情況。被告企業若認為案件複雜等原因,可以要求將此程序轉移到普通的民事訴訟中。然而,若少額訴訟程序繼續進行,企業面臨的最大風險在於其「一次性」的特點。與普通訴訟不同,對於判決無法提出上訴至上級法院,僅能對作出判決的簡易法院提出「異議」。異議申立後的判決是最終的,且具有強制執行力。
民事調解
民事調解是一種由法官和民間專家組成的調解委員會,以中立的立場介入當事人之間,促進通過協商達成自主解決的程序。這一程序是自願性的,只有當事人雙方都願意進行談判和讓步時才能成立。程序是非公開進行的,比起嚴格適用法律,更重視雙方當事人的滿意度,尋求一個符合實際情況的靈活解決方案。
在經營策略上,民事調解是當事人間的對立不是非常嚴重,且希望維持未來關係,或者爭議點在於非金錢性事項如職場環境調整等情況下的有效選擇。然而,如果一方當事人堅持強硬態度不變,調解可能會因此失敗,導致時間和努力白費。
這些簡便的程序,由於其性質,應被視為針對特定情況的工具。少額訴訟的請求金額上限(60萬日元)和民事調解的非強制性質,並不適合解決涉及企業核心的重大勞動爭議,如解雇的有效性或高額未付工資請求。解雇相關的爭議中,未付工資(追溯工資)的金額通常遠超過60萬日元,且當事人間的主張差異過大,使得通過自願協商的調解解決變得困難。因此,經營層應將這些程序視為處理相對重要性較低的純金錢性小規模爭議的有效手段,而不應將其視為解決重大勞動爭議的主要策略。
從日本的裁判例看勞動爭議的實態
為了理解各種程序在實際爭議中如何運作以及它們帶來的結果,審視具體的裁判例子是不可或缺的。以下,本所將解析三種對企業經營影響特別大的典型爭議類型,並探討日本法院的判決及其戰略意義。
不當解僱
在布魯姆伯格・L.P.事件(東京地方裁判所 2012年(平成24年)10月5日判決)中,一家企業以員工的溝通能力、工作速度、數量和質量未達到要求標準為由,以能力不足為理由解僱了員工。然而,法院判定該解僱無效。
這一判決給出的經營教訓是,僅僅主張「能力不足」或「成績不良」是不足以證明解僱合理性的。法院在認定對勞工最為嚴重的不利處分——解僱為有效時,對企業提出了極為嚴格的要求。具體來說,企業必須①基於客觀合理的標準具體證明能力不足的事實,並且②證明為避免解僱,企業已經向該員工提供了充分的指導、培訓或調職等改善機會。這些過程的詳細記錄和客觀證據(如評價記錄、指導記錄、電子郵件等)是企業主張成敗的決定性因素。
未支付加班費
在康正産業事件(鹿兒島地方裁判所 2010年(平成22年)2月16日判決)中,一名飲食店店鋪負責人員工要求支付未給付的加班費。企業方面主張該員工屬於管理監督者,因此無需支付加班費,但法院駁回了這一主張,命令企業支付約732萬日元。
這一案例對所謂的「名義上的管理職」問題敲響了警鐘。企業若要將員工作為勞動基準法上的「管理監督者」對待,僅僅賦予職位名稱是不夠的。法院會嚴格審查實際情況,包括①是否參與決定經營方針、②是否有不受嚴格管理的出退勤自由裁量權、③是否獲得與其地位相符的待遇(如薪資等)。不當的勤務管理或模糊的雇用合約可能會導致企業面臨巨額未支付加班費的財務風險,這一判決清晰地表明了這一點。
職場霸凌
在福井地方裁判所 2014年(平成26年)11月28日的判決中,一名新入社員因受到上司持續的惡言相向(如「死了算了」等)而自殺,法院認定企業及該上司負有責任,判決支付高達約7300萬日元的損害賠償。
這一判決凸顯了企業所承擔的「安全配慮義務」的重要性。企業有法律義務為員工提供一個能夠保障心理和生理安全的勞動環境,忽視職場內的霸凌行為被視為違反這一義務。這一案例表明,霸凌不僅是個人問題,更是組織整體應該共同面對的經營風險。制定有效的防止霸凌規程、對所有員工進行定期培訓、設立員工能夠安心進行諮詢和通報的窗口,以及建立適當的調查和應對流程,對於防止此類悲劇及其帶來的經營損害至關重要。
總結
在日本的司法制度中,勞動爭議解決程序提供了具有不同目的和功能的多樣化選擇。如果優先考慮迅速且非公開的解決方案,則「勞動審判程序」可能是一個有效的選項,但其準備期間的短暫可能會給企業帶來重大風險。另一方面,如果企業想要徹底主張其法律正當性,則「民事常規訴訟」將成為舞台,但必須準備面對長時間、高昂的費用以及公開程序可能帶來的評議風險這些嚴重的代價。此外,「保全訴訟」可能會在爭議的初期階段對企業造成單方面的金錢負擔,因此需要迅速且精準的防禦。而「少額訴訟」和「民事調解」則是處理較小規模金錢爭議的有限工具。最佳策略會根據個別案件的具體事實關係以及企業所優先考慮的事項(速度、成本、保密性或原則的堅持)而有很大的不同。深入理解這些程序的特性並根據情況做出最佳選擇,是有效管理經營上危機的關鍵。
モノリス法律事務所在所有這些司法程序中都擁有豐富的代理經驗。本所的優勢在於深厚的日本勞動法專業知識,以及多名具有外國律師資格的英語使用者的加入。這使本所能夠深入理解在國際業務中運營的企業獨特的文化和經營視角,並能夠用日語和英語提供無縫且高度專業的法律服務。面對勞動爭議這一複雜挑戰時,請務必向本所諮詢。作為您的戰略夥伴,本所將全力支持,保護貴公司的利益,並引導您走向最佳解決方案。
Category: General Corpor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