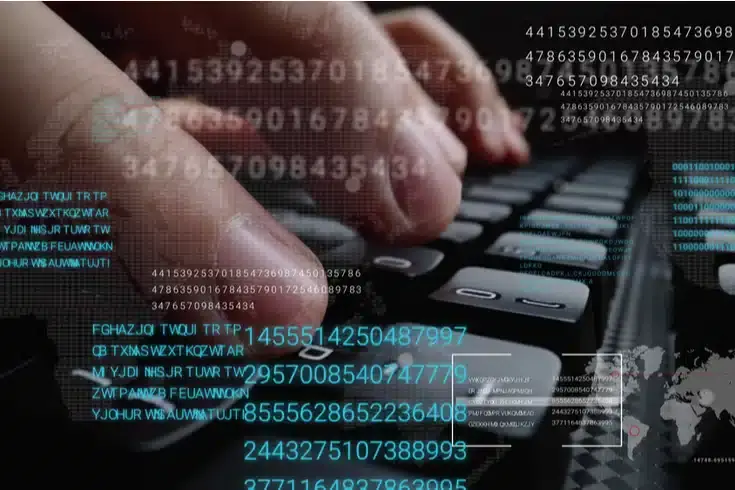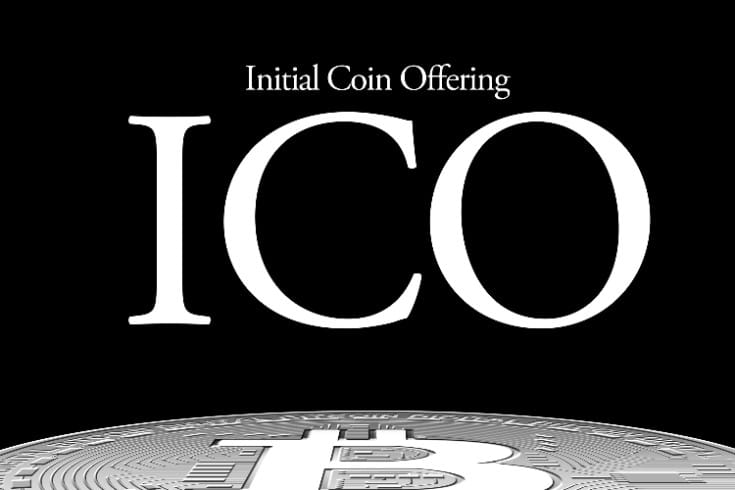在日本勞動法中勞動組合的組織與運營

在日本的商業環境中,勞工組合對企業經營和勞資關係具有重大影響。日本憲法保障了勞工的團結權、團體談判權和團體行動權,基於此,日本制定了勞工組合法等相關法律。因此,企業與勞工組合的互動不是選擇問題,而是必須在法律框架內應對的經營挑戰。準確理解勞工組合的組織結構、運營原則以及規範這些的法律規制,對於建立健全的勞資關係和管理法律風險至關重要。本文將聚焦於日本勞動法下勞工組合的組織與運營,特別是「勞工組合的自治及其法律規制」、「工會商店協定」、「勞工組合的機構」這三個重要方面,從法律基礎和實務角度進行詳細解說。透過這項分析,本所旨在幫助企業管理者能夠策略性地、遵守法令地與勞工組合建立關係。
日本勞動組合的自治及其法律要求
在日本的法律制度中,勞動組合被賦予了高度的自治權。這種自治原則旨在排除國家或雇主對組合內部運營的不當干預,以確保勞動者能夠在與雇主對等的立場上進行談判。然而,為了享受日本勞動組合法所提供的保護,勞動組合必須滿足該法律規定的嚴格要求。理解這些要求對於企業判斷其所面對的團體是否為合法的談判對手至關重要。
日本憲法第28條保障了勞動者的團結權、集體談判權和集體行動權。具體化這些憲法權利的是日本勞動組合法。該法第2條本文將勞動組合定義為「勞動者為主體,自主性地組織起來,以維持和改善勞動條件或其他提升經濟地位為主要目的的團體或其聯合體」。這一定義包含了勞動組合在法律上被認可所需的積極要件,即勞動者為主體、自主性團體以及主要目的是維持和改善勞動條件等。
另一方面,日本勞動組合法第2條但書規定了將某些特定性質的團體排除在勞動組合法適用範圍之外的消極要件。如果一個團體符合這些要件中的任何一項,則在法律上不被視為勞動組合,無法獲得該法賦予的強有力保護(例如,不當勞動行為的救濟)。對企業經營來說,理解這些消極要件尤為重要。
首先,允許代表雇主利益的人參與的團體不被認為是勞動組合。這包括公司高管、擁有直接招聘或解僱、晉升權力的監督職位的勞動者,以及接觸到雇主勞動關係計劃或政策機密的人員。這項規定的目的是保障組合的自主性,排除雇主的影響力。
其次,原則上,從雇主那裡獲得經營費用援助的團體也不被認為是勞動組合。這是為了防止組合在財政上依賴雇主,從而保持獨立性。不過,日本勞動組合法也認可了一些例外情況,例如,雇主允許勞動者在工作時間內無需損失工資就可以進行談判、對福利基金的捐獻,以及提供最小限度辦公空間等,這些不被視為禁止的費用援助。
第三,僅以共済事業或福利事業為目的的團體,或主要從事政治運動或社會運動的團體,也不屬於勞動組合法的適用對象。
這些法律要求不僅僅是定義性規定。當企業被某個團體要求進行集體談判時,確認該團體是否符合日本勞動組合法第2條的要求,並且是合法的勞動組合,是判斷企業法律義務的第一步。如果該團體允許高管參與或從雇主那裡獲得不當的費用援助,則該團體可能沒有法律談判權。因此,仔細審查這些要求是企業法務和風險管理中基本盡職調查的一部分。
組合規約:日本勞動組合內部統治的根本
為了使勞動組合在法律上有效運作,制定組織和運營的基本原則「組合規約」是不可或缺的。組合規約可視為組合內部的「憲法」,它規範了組合成員的權利義務關係和決策過程。此外,日本勞動組合法要求組合規約必須包含特定的民主條款,以符合該法賦予的保護資格。因此,理解組合規約的內容對於評估該勞動組合的運作合法性和民主性至關重要。
根據日本勞動組合法第5條第1項的規定,勞動組合要參與該法規定的程序並獲得救濟,必須向勞動委員會證明其組合規約符合第2項的規定。雖然規約有缺陷的組合(規約不備組合)在參與勞動組合法上的程序方面受到限制,但根據該法第7條第1項,個別勞工的保護並未被否定,且憲法第28條對合法團體行動的保護也是被認可的。
日本勞動組合法第5條第2項要求組合規約必須包含的民主條款,包括以下9項:
- 名稱
- 主要辦公室所在地
- 組合成員有權參與所有組合事務並獲得平等待遇
- 任何人不得因種族、宗教、性別、門第或身份而被剝奪成為組合成員的資格
- 役員應通過組合成員的直接無記名投票選舉產生(對於聯合組合,也可以通過單位組合成員直接無記名投票選出的代表的直接無記名投票產生)
- 總會至少每年召開一次
- 會計報告應至少每年向組合成員公開一次,並附有專業會計審計人的證明
- 同盟罷工(罷工)必須經過組合成員直接無記名投票的過半數決定後才能開始
- 規約的修改必須獲得組合成員直接無記名投票過半數的支持
這些規定旨在確保組合運營的民主性和透明性。例如,要求在役員選舉、罷工決定和規約修改等重要決策中進行組合成員的直接無記名投票,以防止少數幹部的專斷運營,並保障基於組合成員總意的活動。此外,會計報告的公開義務確保了組合財政的透明度,並保證了組合費的正當使用。
這些規約上的要求就像是勞動組合獲得法律力量的「入場券」。當勞動組合對雇主的不當勞動行為(例如,無正當理由拒絕團體談判)提出勞動委員會救濟申請時,勞動委員會首先會確認該組合是否為法適合組合,即其規約是否滿足日本勞動組合法第5條第2項的要求。如果規約有缺陷,申請本身可能會被駁回。這意味著從企業方面來看,當面臨勞動組合的法律措施時,確認該組合的規約是否滿足法庭要求可以成為一種法律對策。組合的內部統治問題不僅僅是組合內部的問題,它也可能成為勞資間法律爭議的重要爭點。
日本勞動組合的機構與權限
為了達成其目標,勞動組合在內部設置了決策機構和執行機構等組織。理解這些機構的組成和權限對於企業在與勞動組合進行談判時,把握誰是合法代表以及組合意志如何決定的過程,是至關重要的。
勞動組合的最高決策機構通常是「大會」(或稱總會)。大會相當於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大會,擁有決定組合運營中最重要事項的權限,如活動方針、預算、幹部選任、組合規約的修改以及勞動協約的締結批准等。根據日本勞動組合法(Japanese Labor Union Act)第5條第2項第6號的規定,大會至少每年必須召開一次。
大會決定的方針由「執行委員會」日常執行。執行委員會由大會選出的幹部組成,包括委員長、副委員長、書記長等。執行委員會負責具體談判的準備、組合員意見的集約以及日常的組合事務,是組合運營的核心。
在這些幹部中,「委員長」通常擔任組合對外代表的最高責任者。日本勞動組合法第6條規定,「勞動組合的代表或受勞動組合委任的人,有權與使用者或其團體就勞動協約的締結等事項進行談判」。因此,委員長等代表有法律保障的權限,可以與使用者進行集體談判。
企業在與勞動組合進行談判時,了解這一機構結構在實務上非常重要。通常參與團體談判的是執行委員會的成員,他們根據日本勞動組合法第6條擁有進行談判的合法權限。然而,他們所擁有的權限僅限於「談判權限」,並不一定等同於「最終妥協權限」。
在許多組合中,組合規約規定,與使用者達成的勞動協約草案最終批准的權限保留給最高決策機構大會。這是一種民主控制機制,以防止談判代表做出違背組合員整體利益的妥協。這種結構對企業方的談判策略有重大影響。即使與執行委員會達成臨時協議,該協議案在後續大會上仍可能被組合員投票否決。因此,企業方的談判代表在談判過程中,確認組合方的內部批准流程並考慮到批准風險,制定談判策略是明智的。
日本ユニオン・ショップ協定的法律架構與實務操作
ユニオン・ショップ協定是在日本的勞資關係中廣泛採用的一種制度,旨在加強工會的組織力量。該協定實際上要求企業員工加入特定的勞工組合,因此準確理解其法律效力與限制對於企業的人事勞務管理至關重要。
根據日本勞動組合法第7條第1項的規定,原則上禁止因為勞工不加入工會或退出工會而對其進行解僱等不利處理,這被視為「不當勞動行為」。然而,該條款的但書設置了一個重要的例外:「如果勞動組合代表了特定工廠或事業場所中過半數的雇員,則可以訂立以成為該工會會員為雇用條件的勞動協約,這不被視為妨礙」。這就是ユニオン・ショップ協定的法律基礎。
該協定最重要的有效要件是「過半數代表要求」。只有在該事業場所的勞工過半數組成的工會(過半數工會)才能締結ユニオン・ショップ協定。即使在協定締結時工會佔有過半數,如果後來因為工會成員的退出而不再佔有過半數,ユニオン・ショップ協定將自動失去效力。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基於員工不加入工會的理由進行解僱的義務將消失。
即使勞動組合提出締結ユニオン・ショップ協定,企業也不必一定同意最嚴格的條款。根據談判情況,企業也可以選擇締結更為寬鬆、保留企業自主權的協定形式。在實務操作中,常見的類型包括以下兩種:
一種是被稱為「尻抜けユニオン」的形式。在這種協定中,雖然原則上規定退出或被除名的工會成員應被解僱,但最終的解僱決定留給公司和工會協商,從而保留了企業的裁量權。
另一種是「宣言ユニオン」。這種協定僅僅宣稱「員工必須是工會成員」,而不對基於非工會成員身份進行解僱的義務進行任何規定,是效力最弱的形式。
為了清晰區分ユニオン・ショップ協定與其他相關制度的差異,以下表格進行了整理。雖然這些制度在國際上也被採用,但在日本法律中的有效性各不相同。
| 協定類型 | 定義 | 員工的工會加入義務 | 在日本法律中的有效性 |
| オープン・ショップ | 將是否加入工會完全留給員工自由意志的制度。 | 無 | 有效 |
| ユニオン・ショップ | 在被聘用後的一定期間內,加入特定工會成為繼續雇用的條件。 | 有 | 在特定要求下(如過半數代表)有效 |
| クローズド・ショップ | 在聘用時就要求必須是特定工會的成員。 | 聘用的前提條件 | 原則上無效(僅在極限情況下,如特定職業工會,有例外) |
如此比較可見,在聘用階段就要求工會成員資格的クローズド・ショップ在日本原則上是不被認可的。相反,ユニオン・ショップ在嚴格的過半數代表要求下才被認為是有效的制度。企業在考慮締結ユニオン・ショップ協定時,必須充分理解這些法律要求和實務上的選擇,並根據自身勞資關係的實際情況做出謹慎的決策。
關於日本ユニオン・ショップ協定的重要裁判例
ユニオン・ショップ協定為勞動組合提供了堅實的組織基礎,同時對個別勞工的雇用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因此圍繞其運用產生了許多法律爭議。日本的最高法院透過一系列判決明確指出,ユニオン・ショップ協定的效力存在法律上的限制。這些判例對於企業理解基於協定執行解雇義務時的法律風險至關重要。
首先,有關組合無效除名情況下解雇的效力的判例。在日本食塩製造事件(1975年4月25日最高法院判決)中,最高法院指出,勞動組合若不當地除名組員,則雇主以此無效的除名處分為由解雇該勞工,屬於濫用解雇權且無效。此判決對企業提出了重要的警示:企業不應僅僅作為執行組合要求的「執行機關」。在執行解雇前,企業有法律上的義務進行一定的調查和確認,例如組合的除名程序是否按照組合規約正當進行,除名理由是否合理等。若忽視這些義務,基於不當除名進行解雇,該解雇將被認定無效,企業將面臨對該員工的法律責任。
其次,有關加入其他勞動組合後解雇效力的重要判例。三井倉庫港運事件(1989年12月14日最高法院判決)中,最高法院裁定,若勞工退出與ユニオン・ショップ協定締結的多數派組合,並立即加入其他少數派組合或新成立組合,雇主無需承擔解雇該勞工的義務。最高法院認為,ユニオン・ショップ協定的目的在於維持和加強組合的團結力,但這不應侵犯勞工更根本的權利,即選擇組合的自由。因此,即使勞工退出多數派組合,只要他們加入其他組合維持勞工團結,對其提出的解雇要求違反了日本民法第90條所定的公序良俗,因而無效。
這些判例極為重要,因為它們明確了ユニオン・ショップ協定效力的限制。該協定對於未加入任何組合的勞工具有促使其加入多數派組合的效力,但不具備阻礙勞工從一個組合轉移到另一個組合的自由。特別是在企業內存在多個勞動組合的情況下,這些判例在法律上保護了少數派組合的存續。
這兩項最高法院的判決共同點在於,法院在ユニオン・ショップ協定的契約效力與勞工個人的基本權利(如接受適正程序的權利、團結權和選擇組合的自由)之間進行了謹慎的利益衡量。這種司法態度向企業經營者示意,ユニオン・ショップ協定不是自動的解雇裝置。基於協定的解雇行為具有高度的法律風險,並可能成為法院事後審查的對象。因此,在考慮進行此類解雇時,務必事先尋求專業法律家的建議。
總結
在日本的勞動法體系中,勞動組合的組織與運營受到詳細的法律框架規範,以尊重組合自治的同時,保證其活動能夠民主且公正地進行。從企業經營的角度來看,準確理解勞動組合獲得法律保護的資格要求、組合規約中應規定的民主運營原則,以及像工會商店協議這樣的組織強制制度所具有的強大效力及其法律限制,是建立穩定且建設性的勞資關係的基礎。這些法律知識將成為在進行集體談判、簽訂勞動協約以及做出人事勞務相關決策時,避免法律風險、做出適當經營判斷的指南針。
Monolith法律事務所擁有豐富的實績,為國內外眾多客戶企業提供了關於日本勞動法的複雜問題解決方案。本所事務所擁有多名具有日本律師資格以及外國律師資格的英語律師,能夠應對國際商業環境中出現的多樣化勞務問題。無論是勞動組合的組織與運營諮詢、集體談判的應對,還是勞動協約的審查等,本所都能提供涉及本主題的全方位法律支持。
Category: General Corpor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