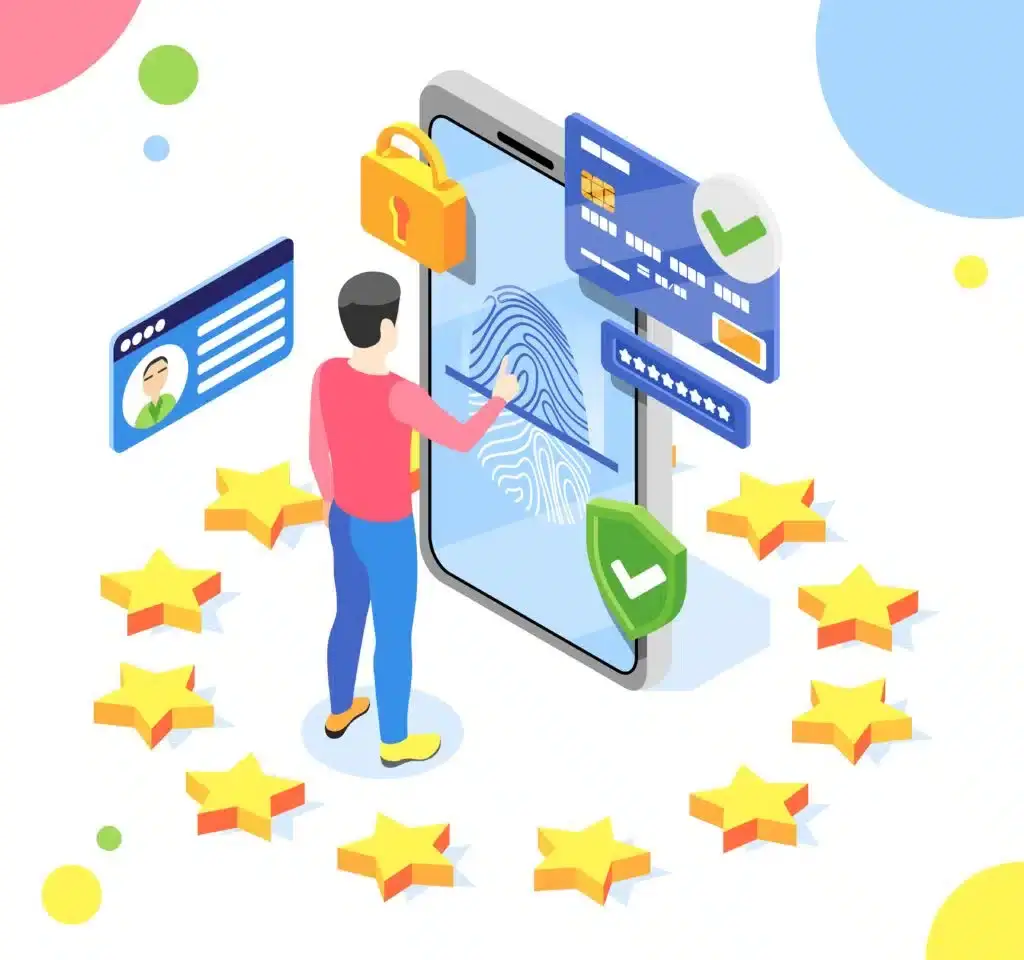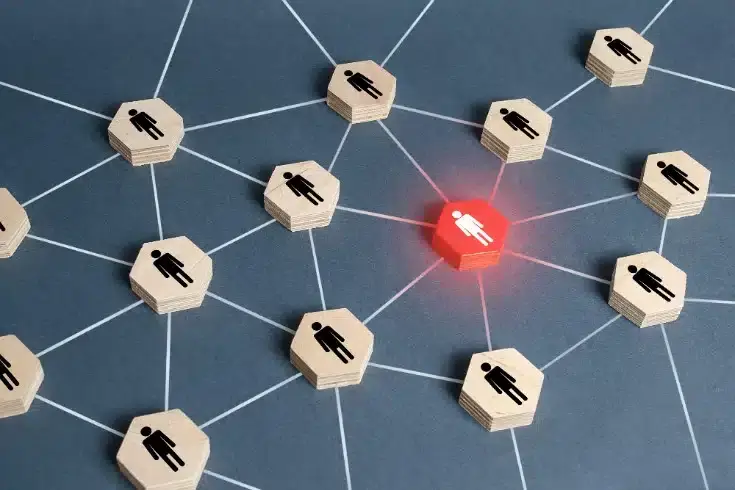日本公司法中董事的善意管理注意義務與經營判斷原則

在日本的企業治理中,董事在確保公司成長與持續性方面扮演著核心角色。這一角色伴隨著對公司的重大法律責任。其中特別重要的是「善意管理注意義務」與「經營判斷原則」這兩個概念。這些概念為董事執行職務時所需遵循的注意標準,以及其判斷在事後被追究時的責任範圍。日本公司法對董事施加了高標準的注意義務,同時為了不阻礙對企業經營不可或缺的風險承擔,也要求尊重經營判斷。
本文旨在解說日本公司法下董事的善意管理注意義務與經營判斷原則,包括其定義、法律依據,以及在日本司法案例中的具體應用。通過基於日本法律並結合實際案例,本文旨在闡明這些原則如何被解釋和應用,從而加深對日本企業治理的理解。
在日本公司法下董事的善意管理注意義務
日本公司法與善管注意義務
根據日本公司法,取締役因受公司委任執行職務,對公司負有「善管注意義務」。該義務指的是根據個人社會地位所普遍要求的注意義務。日本公司法第330條規定,「股份有限公司與其役員及會計監査人之間的關係,應遵循委任相關規定」,因此,日本民法第644條中的善管注意義務也適用於取締役。日本民法第644條規定,「受任者應依委任的本旨,以善良管理者的注意,處理委任事務」。這意味著取締役需充分運用自身知識與經驗,盡最大努力保護公司(股東)的最大利益,這是一項相當嚴格的義務。
在日本公司法下的善管注意義務要求取締役遵守民法上委任契約中「善良管理者的注意」這一高標準。這一標準不僅要求取締役避免疏忽,還要求他們充分運用專業知識與經驗,積極為公司利益行動,承擔「專業人士的注意義務」。這種高度的義務對於理解日本企業治理中個人責任的重要性至關重要。取締役不能僅以「不知情」為由逃避責任,他們有責任積極收集、分析信息並作出判斷,這是善管注意義務的本質所在。
與善管注意義務密切相關的是「忠實義務」。日本公司法第355條規定,「取締役應遵守法律、公司章程以及股東大會的決議,忠實地執行其職務」。忠實義務要求取締役將公司利益放在首位,不得為自身或第三方利益不當使用公司的專有知識等。日本最高法院認為,忠實義務是對善管注意義務的延伸和明確化,並非與一般委任關係中的善管注意義務「不同的高度義務」(最高法院昭和45年(1970)6月24日判決)。這一解釋意味著,在實務中,取締役不需單獨考慮兩種不同的義務,而是應在善管注意義務這一綜合框架內忠實行動。日本最高法院將忠實義務定位為善管注意義務的明確化,並非另一高度義務,這意味著取締役無需在兩種不同義務間進行複雜的調整。這種整合的方法為取締役為公司最佳利益行動時提供了更清晰、統一的行為準則,提高了法律遵從的可預測性。
違反善管注意義務的董事所承擔的責任(Under Japanese Corporate Law)
當董事違反善管注意義務時,可能會承擔各種責任。最直接的是對公司的損害賠償責任,即「任務懈怠責任」。日本公司法(Japanese Companies Act)第423條第1項明確規定:“董事、會計參與、監事、執行官或會計監察人(以下在本章中稱為「役員等」)若怠於其任務,則應對股份公司賠償因此造成的損害。”這適用於董事在執行職務時忽略善管注意義務,給公司造成損害的情況。損害賠償的範圍限於與義務違反行為存在「相當因果關係」的損害。
此外,如果董事違反善管注意義務是出於惡意或重大過失,則可能對公司以外的第三方承擔損害賠償責任。日本公司法第429條第1項規定:“役員等在執行其職務時若存在惡意或重大過失,則應對因此給第三方造成的損害承擔賠償責任。”這一規定被解釋為出於政策考量,以防止在公司無資力的情況下第三方遭受不可預見的損害而設立的特別法定責任。善管注意義務違反可能導致對公司的任務懈怠責任,以及在存在惡意或重大過失時對第三方的損害賠償責任,甚至可能導致被解任,這表明董事個人面臨的法律風險極高。這種高風險強調了董事在進行經營判斷時,徹底的盡職調查、決策過程的透明度以及適當的記錄保存的重要性。即使結果不盡如人意,如果有適當過程的證據,也有可能避免責任,因此在決策過程中明確記錄決策依據和過程,對董事的自我保護至關重要。
同時,違反善管注意義務的董事也可能被股東大會決議解任。日本公司法第339條第1項規定:“役員及會計監察人可以隨時被股東大會決議解任”,而日本公司法第341條則規定了解任決議的要求。
經營判斷原則及其適用
什麼是經營判斷原則
企業經營總是一連串伴隨不確定性和風險的決策過程。董事需接受股東委託,行使廣泛的自由裁量權,並需要做出涉及風險的決策,如新業務拓展或併購。然而,若這些決策最終導致公司損失,董事可能會因違反善意管理義務而受到質疑。因此,「經營判斷原則」便是在此情況下,用於判斷董事的經營決策法律責任的基準。
經營判斷原則認為,只要董事在做出經營決策時,對事實的認識沒有重大疏忽,且決策內容不是極度不合理,就不應該認定其違反了善意管理義務或忠誠義務。這一原則的目的是為了讓經營者能夠無所顧忌地專注於冒險以提升企業價值的經營活動。
經營判斷原則旨在尊重董事行使風險決策的自由裁量權,以免其因擔憂而猶豫不決。然而,日本最高法院對這一原則持謹慎態度,並未積極支持將其作為明確的法律規範。這表明董事不應將經營判斷原則視為萬能的免罪符。相反,即使結果不盡如人意,董事也必須具體證明其決策過程和內容是合理的,這一原則只有在嚴格的盡職調查和透明的決策過程中才能發揮防禦作用。這意味著,董事不會完全免於「結果責任」,反而可能會嚴格追究「過程責任」。因此,董事在決策過程中進行信息收集、分析、專家諮詢以及董事會討論等,將這些作為證據留存下來是極其重要的。
「經營判斷原則」與日本法院的態度
在適用經營判斷原則時,日本下級審法院的案例顯示,法院會區分「決策過程」(程序面)和「決策內容」(內容面),並對過程面施加嚴格的審查標準。這表明對董事而言,決策「過程」的重要性不亞於「結果」,甚至更為重要。這意味著董事在做出經營決策時,必須徹底收集信息、聽取專家意見、進行風險評估,並將所有這些過程適當記錄和文檔化,這將成為對抗未來責任追究的有力防禦。由於法院在評估董事決策的合理性時重視決策過程和信息收集,董事必須清晰地說明決策的「為什麼」和「如何」,並留下證據,這是無論結果如何都能免於責任追究的關鍵。
日本最高法院對經營判斷原則持謹慎態度,並未積極支持。最高法院傾向於不直接使用「經營判斷原則」這一術語,而是根據個案判斷決策的合理性。這可能受到過去經營判斷原則被濫用作為董事免責的「免罪符」的影響。最高法院的這一立場暗示董事不應過度依賴經營判斷原則作為絕對的防護,而應始終準備好證明其決策客觀上是合理的。日本最高法院對經營判斷原則的謹慎態度,以及下級審法院對判斷框架的持續討論,表明這一法理仍在發展中,未來其解釋可能會發生變化。這種動態狀況意味著必須持續關注最新的案例和學說動向,並相應調整企業治理實踐。
從日本的裁判例看善管注意義務與經營判斷原則
為了理解善管注意義務與經營判斷原則在實際的日本裁判中如何適用,審視具體的判例是至關重要的。本文將介紹兩個特別重要的日本判例。
日本サンライズ事件判決(東京地方裁判所1993年(平成5年)9月27日判決)
株式会社A社是一家以大樓租賃業務為主的小型公司。為了消除赤字,代表取締役Y1決定進行當時流行的股票投資(信用交易),並投入大量借款進行股票投資。在公司章程中增加了有價證券交易後,最初確實獲得了利潤,但由於股價暴跌,A社遭受了相當於投資金額70%的巨大損失。股東X對代表取締役Y1以及未能妥善監督的常勤取締役Y2和取締役Y3提起了股東代表訴訟,要求賠償損失。
東京地方裁判所認定代表取締役Y1違反了善管注意義務,並支持了賠償請求。判決指出,Y1雖然能夠預見到股價波動可能導致公司遭受損失和經營危機,但他輕視了這種可能性,投入大量借款,導致公司遭受了威脅到本業存續的損失。特別是對於新業務,判決認為,考慮到公司的規模、業務性質和營業利潤等因素,如果存在造成難以恢復的損失的風險,且該風險是可以預見的,則應避免進行這種新業務,這是取締役應負的善管注意義務。此外,判決還認為A社進行股票投資的必要性是無法認可的。對於常勤取締役Y2和取締役Y3,判決也肯定了他們對代表取締役Y1行為的監督義務違反。
本判決雖然承認企業經營具有冒險性,但也展現了對取締役行為責任的嚴格判斷態度。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考慮是否適用經營判斷原則時,區分了決策過程(程序面)和決策內容(判斷面)。判決對投資的事前事後調查以及公司的資力和規模的平衡等程序面,以及股票投資必要性的判斷面進行了分開考量,這種明確的方法被認為是創新的。這表明,當取締役進行涉及風險的經營決策時,其決策過程是否適當將受到嚴格審查。該判決向外界發出了一個明確的信號,即在評估取締役的經營決策時,法院不僅關注結果是成功還是失敗,而且重視決策是基於何種信息、通過何種程序、經過多少考慮而作出的。這種「重視過程」的態度強調了取締役在未來可能被問責時,能夠證明自己遵循了適當程序的重要性,並強調了詳細記錄會議記錄和相關資料的實務重要性。
AIJ投資顧問年金資產消失事件判決(日本東京地方裁判所2016年(平成28年)7月14日判決)
A公司是一家從事證券銷售等業務的公司,其代表取締役b與C公司的代表取締役d共謀,利用虛假的基金淨資產值(NAV)進行銷售活動,從而管理年金資產。這一詐騙行為導致基金蒙受巨額損失。購買該基金的年金基金,指控A公司的社外取締役Y1和常勤監査役Y2未能履行對代表取締役違法行為的監督和審計義務,因此提起了損害賠償訴訟。
日本東京地方裁判所未認定社外取締役Y1和常勤監査役Y2有監督和審計義務的違反。法院認為,取締役的監督義務基於過失,只有在能夠發現非法業務執行的情況下,且取締役知悉該情況時,才能確認其責任。在本案中,法院對原告提出的取締役應該懷疑的各種情況,包括基金的運營業績、業界雜誌的文章、解約請求的情況以及融資案件等,進行了具體事實關係的詳細審查。結果認為,僅憑這些情況,不足以判斷Y1和Y2認識到使用虛假NAV的銷售活動或對此產生疑問。
這一判決重要之處在於,它表明了取締役,特別是社外取締役和監査役的監督和審計義務並非無限擴大。取締役被要求根據合理可知的信息履行注意義務,但並不意味著他們有預見和發現所有不正行為的義務。這一界限的明確,與防止因過度嚴格的取締役責任而導致優秀人才猶豫不決擔任取締役職位的「取締役萎縮」現象相符,這也符合經營判斷原則的宗旨。該判決意味著,對取締役的判斷不是基於他們掌握所有信息的前提,而是基於他們「合理可接觸的信息」。雖然取締役可能因信息不足而免責,但企業有責任建立堅固的內部控制系統,確保重要信息(特別是風險和不正行為的跡象)不被隱瞞,並適時傳達給取締役,以便他們能夠適當履行其義務。這一判決間接地指出了這一點。
日本法庭思維的裁判例示
在日本的「日本サンライズ事件判決」中,法院對於因投機性股票投資導致的巨額損失,嚴格認定了董事的善管注意義務違反。該判決重視了根據公司規模和業務性質所能預見的風險,以及缺乏進行該業務的「必要性」。相對地,在AIJ投資顧問年金資產消失事件判決中,否定了社外董事和監察役的監督義務違反。該判決強調了董事義務僅限於「合理可發現的情況」,並判斷不負有預見所有不正行為的義務。這兩個判決顯示了日本法院在善管注意義務是高度義務的同時,其違反的認定基於具體情況下的「合理性」和「預見可能性」,是一種平衡的方法。在日本サンライズ事件中,法院嚴厲指出董事「儘管能夠預測」卻忽視了風險,並進行了沒有「正當化必要性」的業務,從而認定了其責任。這是對董事應積極避免風險,將公司存續放在首位的強烈訊息。而在AIJ事件中,對於社外董事和監察役是否「認識或應當認識到」或至少「應當懷疑的情況」,應用了該標準,最終因為「沒有發現或應當懷疑的情況」而否定了其責任。這表明了董事的義務不是無限的,而是基於合理範圍內的信息收集和判斷。這種對比清晰地暗示了日本法院在個別情況下,不是單純的結果責任,而是根據行為的「合理性」和「預見可能性」來判斷董事責任的實務判斷標準。
總結
在日本公司法下,取締役的善管注意義務與經營判斷原則是現代企業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兩大概念。善管注意義務要求取締役以「善良的管理者」的高度注意為公司服務,違反此義務可能會對公司或第三方帶來嚴重的法律責任。另一方面,經營判斷原則尊重取締役的裁量權,使其能夠無畏風險地進行創新決策。日本法院在平衡這兩項原則時,特別強調決策「過程」的合理性與謹慎性。日本Sunrise案件判決嚴格審視了取締役的判斷過程和必要性,而AIJ投資顧問年金資產消失事件判決則通過限定監督義務的範圍為合理的知識可能性,為其應用提供了具體指導。
深入理解並遵守這些原則對於在日本經營業務的公司和個人至關重要。日本的法律制度複雜,其解釋和應用因個別案件和法院的判斷而具有多樣性。Monolith法律事務所擁有豐富的日本企業法務實績,特別是在涉及取締役責任和企業治理的主題上,支持了眾多客戶。本所事務所擁有多名具有外國律師資格的英語使用者,能夠從國際視角理解日本複雜的法規,提供實踐性的建議。如果您對日本公司法有任何疑問,或者在企業治理、取締役責任方面有具體咨詢需求,請聯繫Monolith法律事務所。本所將運用專業知識全力支持您在日本的業務活動順利進行。
Category: General Corporate